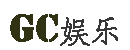第一次長沙會戰前中日軍力大對比,薛岳對陣岡村寧次!
在正面戰場,侵華日軍的歷史幾乎就是第11軍的歷史。
1939年的日軍在中國依舊殘酷地繼續著殺戮、強奸、掠奪、縱火,日復一日的罪行讓“鬼子”這個稱呼是如此的名副其實。他們狂熱而麻木,新兵雖然對過于血腥的場面感到戰栗,但打過幾次活靶子之后也就慢慢無動于衷了。在軍國陰影之下,從鬼回歸到人不那么容易,但他們卻證實著從人變成鬼的簡單。

從殘暴本質的角度看,日軍是沒什么變化的;但從戰力的角度看,1939年的鬼子稍微出現了一些狀況,這主要體現在兵力結構上。
在中國大陸的日軍,現役士兵(1935年到1937年入伍的)只占11%;剩下的89%都是預備役、后備役和補充役士兵,其中后備役士兵又占一半(1920年到1929年入伍的高齡士兵)。這樣算下來,歲數最大的士兵已在40歲左右,其戰力跟侵華之初的日軍相比已經有所下降了。

至于重慶政府這邊,軍事委員會在1939年春把部隊一分為三:正面部隊(潼關、洛陽、鄭州、襄陽、長沙、衡陽連線,在這一線,與日軍東西對峙)、游擊部隊(在日戰區活動)、整訓部隊(以貴州、成都、天水等為訓練基地)。正面部隊和整訓部隊互相輪換,一支部隊打一段時間,就撤下去整訓,隨后整訓部隊又再頂上去,如此循環作戰,以保證戰斗力不出大問題。
為應對相持階段后的戰局,蔣介石在1938年底于南岳衡山開辦了游擊干部訓練班,由善打運動戰的湯恩伯出任教育長,并邀請中共方面的葉劍英出任副教育長,國共攜手培訓游擊干部人才。但三個月后,由于江北日軍調動頻繁,一場新的大戰在所難免,湯恩伯便奉命帶著第31集團軍北返。

就在湯恩伯率軍返回江北時,岡村寧次已下令攻擊南昌了。
占領南昌對日軍來說是武漢會戰期間的一個任務,只因當時第106師團受困萬家嶺而沒能完成。
南昌屬于第9戰區所轄,司令長官陳誠,由薛岳代理,副司令長官羅卓英、楊森、王陵基,參謀長施北衡(保定陸軍軍官學校2期,浙江縉云人),戰區的集團軍總司令有關麟征、商震、盧漢等人,主力部隊有俞濟時第74軍、李覺第70軍、夏楚中第79軍、彭位仁第73軍、歐震第4軍、張耀明第52軍、陳沛第37軍、霍揆彰第54軍、傅仲芳第99軍。
武漢會戰后,第9戰區已成為兵力最雄厚的一個戰區,薛岳掌握的部隊超過50個師,分布在湖南全境、湖北南部以及江西西北部。

如此一來,本就性格剛烈的薛岳,就更加不服管了。
對薛岳來說,他只對陳誠和蔣介石負責。陳在薛不得志時,兩次有恩于他,所以薛脾氣雖大,但對陳非常尊敬。
至于何應欽,則完全不在薛岳眼里。何以參謀總長的名義向薛發公文,薛如覺得內容不合己意,往往會直接在上面批上“不理”“胡說”這樣的詞。何應欽一點辦法沒有。
白崇禧同樣降不住薛岳,雖然他是薛的頂頭上司(白是桂林行營主任,負責督導長江以南各個戰區)。這里面有兩個原因:一是北伐時,薛是第1師師長,白是薛的上級,在上海時,白撤過薛的職,后來兩人關系一直不怎么樣;二是薛跟陳誠關系密切,白是陳潛意識中的對頭。再加上薛岳的壞脾氣,以及廣東人對廣西人的不服,所以薛根本不買白的賬,使得后者發來的公文跟何應欽一個待遇。
據第9戰區參謀處副處長趙子立回憶,有時候,就是面對蔣介石發來的公文,薛岳覺得不對的或有問題的,也會批上“存”或“待辦”,然后束之高閣。
一句話,在作戰上,薛岳基本上不受上級限制,只要他同意,幕僚就可以放膽辦事。
如果在軍情判斷上沒失誤,那么有如此風格的長官,確實是參謀和部隊長的幸運。當然,享有這種幸運的同時,也得做好隨時挨數落的準備。因為薛岳脾氣太急,手下的參謀或其他幕僚,如果一句話說不到點子上,薛岳就開始皺眉頭;假如第二句話仍有點昏,那么他就開罵了。也就是說,在薛岳手下做事,心理素質得好,人得聰明、反應快。
對薛岳來說,他也堅信自己是個聰明人,至少在指揮作戰上是這樣。但事實上,“聰明”這個詞不足以完全形容薛岳,更適合他的詞是“執拗”。正像上面說的那樣,如果在軍情判斷上沒有失誤,執拗自然不失為一名戰區司令長官的優點;但話又說回來,一旦判斷有誤,執拗就是剛愎自用了。幾年后的長衡會戰是個最好的例子,薛岳最終為自己的個性付出了慘重代價。

薛岳的對手岡村寧次,也就更為詭計多端了。
這一次,岡村必取南昌,在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一是可掐斷浙贛鐵路(浙贛鐵路是第3戰區跟大后方聯系的樞紐);二是可切斷安徽、浙江通往江西腹地的通道;三是南昌有中國空軍重要的機場,如果這個基地在,就可以以最短的距離襲擊長江航道上的日軍艦船;四是在第3戰區和第9戰區間砸進一個釘子。
至于打南昌的部隊,岡村力排眾議,堅決使用分別在廬山、萬家嶺有過丟人戰績的第101師團和第106師團。前者師團長,由齋藤彌平太(曾任職關東軍,女諜川島芳子的初婚媒人,后在偽滿出任拓殖公社總裁,戰后在東北失蹤)取代了伊東政喜;后者師團長仍是在萬家嶺被中國軍隊打得膽戰心驚的老鬼子松浦淳六郎。
岡村這樣做,連他的作戰主任參謀宮崎周一都反對。不過,岡村沒聽宮崎的,他同樣固執己見。這叫東京軍部的人不禁竊竊私語。
按岡村的說法,這樣做是要“挽回兩個師團的名譽”。在此之前,岡村給國內熊本留守部隊的負責人寫了封信,叫他轉告熊本、宮崎、大分、鹿兒島四個縣的知事(即縣長):“第6師團已成為日本第一的強大師團,第106師團成了日本第一的軟弱師團。”

老謀深算的岡村當然不會冒失地使用那兩個師團。
在戰術上,他上了雙保險,策應南昌攻略、掩護主力側背的,是第106師團的“表哥”,稻葉四郎的熊本第6師團。有第6師團壓陣,前方日軍的心里會穩當點。此外,他還采取了聲東擊西的計策,叫江北的藤江惠輔第16師團做出佯攻湖北漢水一線的姿態。
武器配備上,岡村不同尋常地為兩個師團配備了將近300門大炮。指揮官是炮兵專家澄田賚四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4期,愛媛縣人)少將。后來,在向南昌攻擊的過程中,炮兵數量一度快追平步兵部隊。這是八年中,日軍炮兵配屬比例最高的一次戰役。
在岡村看來,他必須百分百地給第106師團和第101師團以勝算。如果沒有一場“恢復信心”的戰役,以后這對難兄難弟還不知道會鬧出什么幺蛾子呢。
按岡村的計劃,打南昌,是在鄱陽湖登陸的少量部隊的策應下,以一百多輛坦克為先導,主力沿南潯線進行的一個機甲奔襲戰。
三十四年前的3月10日,日軍取得奉天會戰的勝利,奠定了日俄戰爭的勝局。后來,日本人把這一天作為陸軍紀念日。岡村把攻占南昌的日子,就定在了1939年3月10日。可進入三月,江西雨季提前到來,道路泥濘難行,岡村只好往后推遲了一周。
開戰前,南潯線沉寂得有點反常。
就在薛岳計劃調部隊北上增援漢水一線時,日軍的作戰意圖率先被重慶識破了。在軍令部作戰廳長劉斐呈部長徐永昌的報告中,提到這樣一句:“第9戰區之敵有先行攻占南昌之企圖,現已判明。”
根據軍令部的敵情判斷,蔣介石下了道命令,要薛岳在贛北方面出動部隊,先發制人。
薛岳接報后,認為做這件事有困難,出動大部隊正面強擊,不如以少量部隊進行側擊,所謂“斗智不斗力,出奇不用正”,擱置了蔣介石的計劃。

跟日軍硬碰硬,中國軍隊的戰力確實沒到那一步,且武漢會戰后各部隊都在休整(其實,在戰時,不可以以休整為借口,因為仗隨時都在打)。但是,蔣介石先發制人的決策,重點在于打亂日軍部署。
盡管如此,薛岳還是沒有執行。
日軍那邊,推遲一周后,3月17日,發動了侵占南昌之役。
打南昌要渡過修水(修水后面還有潦河、贛江)。在修水布防的是羅卓英第19集團軍,從西到東:李覺第70軍、劉多荃(保定陸軍軍官學校9期,遼寧鳳城人)第49軍、夏楚中第79軍。李與劉的防線以張公渡為界,劉與夏的防線以饅頭山為界。
作為陳誠“土木系”(按郭汝瑰回憶,“土木系”的“木”,指的是第18軍沒錯,但“土”說的不是陳誠的起家部隊第11師,而是陸軍大學第11期畢業生。這一期畢業生有方天、劉云瀚、李仲辛、劉勁恃、李樹正、石祖黃、周朗等人,多有黃埔6期和黃埔7期背景)的二號人物,羅卓英是比較穩健的,要換個詞呢,就是說挺保守的。比如,每次作戰,他手里都掌握著大量預備隊。有人說了,這是優點啊,太會打仗了。可如果后方預備隊人員在數量上逼近一線部隊,就有點怪了。
南昌會戰中,羅卓英的一線部隊和預備隊之比,有的已達到三比二。而且,預備隊和一線部隊間缺乏第二道防線,兩部前后距離亦過長。這是個致命傷。夏楚中第79軍是個甲級軍,轄三個師,在決定鞏固修水一線后,實際上頂過去的只有一個第76師,后面兩個師蟄伏在修水、贛江形成的三角區,這兩個師跟第一線距離多遠呢?即使急行軍也得跑一天。
更要命的是,從一開始,中國軍隊就判斷錯了敵情。
第9戰區司令長官部預判:日軍若強渡修水的話,進攻方向必然是修水東段(即張公渡以東),因為東段以平地為主,西段則是復雜的山地,不利于日軍行動。基于這種判斷,布置兵力時,重點放在了東段。
沒想到,岡村寧次放過平坦的東段,而把攻擊重點定在以張公渡為突破點的崎嶇的西段。
修水西段防線薄弱,同樣沒有縱深配置。對這一點,身在張公渡以西守備的第70軍第107師的鄒繼衍連長深感憂慮。他們師原本駐防浙東,1938年冬調赴贛北修水。面對整個呈一字長蛇形的野戰工事,鄒繼衍和他的戰友在壕洞口里蹲了一百來天,用他的話說:“面對這種情況,一些受過軍事養成教育、稍具頭腦的下級軍官,也都認識到像我們這樣一字長蛇陣的河防配備,既少縱深,又無重點,處處設防,處處薄弱,突破一點,全線皆垮……”
進入3月中旬,鄒繼衍終于聽到日軍的炮聲。
鄱陽湖邊的古鎮吳城此時也遭到日軍水上攻擊。商震第32軍與登陸日軍展開巷戰。修水一線,東段涂家埠首先遭襲擊,主力日軍則攻向西段張公渡,槍聲十分密集。

修水東段雖不是日軍攻擊重點,但由于一個大隊從夏楚中、劉多荃的接合部饅頭山突入,使兩軍陷入慌亂中。夏、劉二人互相認為是對方過早失去陣地而使自己的部隊陷入被動。
夏楚中說:“我的部隊被迫撤下來,因為左翼第49軍第105師王鐵漢(‘九一八’事變時駐沈陽北大營,任東北軍獨立旅第七旅620團團長,打響當夜第一槍)的陣地過早丟失。”
劉多荃馬上反駁,說:“我的部隊丟了陣地,跟右翼夏楚中部被日軍包圍有關。”
南昌會戰從一開始,中國軍隊就陷入被動。但日軍亦有勝之不武處:強渡修水前,除進行三四個小時的炮擊外,還在10分鐘內發射3000枚毒氣彈,其中多是噴嚏式瓦斯彈,頂在一線的第79軍第76師師長王凌云(中央軍校高教班,河南洛陽人)和手下的旅長、團長幾乎都中了毒氣,士兵們的情況可想而知。

自武漢會戰以來,侵華日軍頻頻卑劣地使用毒氣彈。
毒氣戰中,鬼子主要使用催淚性苯氯乙酮瓦斯(一旦呼入,人體呼吸系統和內臟即受傷)。此外,還有嘔吐性毒氣以及糜爛性芥子氣(對眼睛、呼吸道和皮膚傷害極大)、氯乙烯氯砷(即路易氏氣。皮膚中毒后,在灼痛感下,出現紅斑、水泡及至腐爛;人體吸入后,則破壞整個呼吸系統)。
第76師的陣地上黃色的毒煙彌漫,在其籠罩中,日光也慘淡下去。

該師老兵蘇有才回憶,他所在的那個連,從連長往下全部被毒氣熏倒,咳嗽聲響遍整個陣地。他看著戰友的血從鼻子里淌出來。在驚訝的同時,卻不知自己的血也已流出來:“那種難受勁兒,沒經歷過的人是永遠也想不到的。”
會戰前,岡村寧次給此戰定性為奔襲戰,以“快”字當頭。
渡過修水后,日軍棄左右兩翼的中國軍隊于不顧,以坦克部隊為前鋒,沿尚未被破壞的九江到南昌的公路直下而去。
我們說過,日軍的坦克,比如“94式”,猶如超級玩具,這玩意放在歐洲戰場,不堪一擊,但在中國士兵面前,卻有很大的威懾力。中國軍隊的一道道陣地就是這樣被撕破的。跟進的日軍步兵攻占南昌外圍的安義后,又佯攻一旁的奉新。就在羅卓英組織兵力爭奪奉新時,穿過安義的坦克部隊已在贛江大橋前等著第101師團了。
關于南昌沒辦法保全這件事,作戰廳長劉斐在判斷軍情時已講到:“依過去作戰經驗,敵之補充圓活、裝備優越,如其堅持某一要點或某一要線時,我軍至最后亦難保不失……”同時,劉斐也提了一句,“我軍戰力消耗至如何程度,即應決心放棄南昌?”
劉斐的意思是:對沒必要決死保衛的城市,只要周邊部隊消耗到二分之一,即可放棄該城,轉移勢態。他解釋道:“如部隊不打到消耗二分之一,那么就不能消耗敵人;如不保存剩下的二分之一,就不能保證持久戰打下去。”
情急之下,守備南昌的商震派出一個爆破組,冒著日軍坦克的炮火炸毀了贛江大橋。但那個爆破組的戰士,多數都為國犧牲了。
一天后,趕到的日軍第101師團開始強渡贛江。
羅卓英的電話這時候也從上高打來,跟薛岳說:“南昌必將不保。”
薛岳叫來參謀處長狄醒宇(黃埔軍校4期,江蘇溧陽人)和副處長趙子立,叫兩人擬定撤退令。
狄、趙二人互相看看,都不同意立即就撤,認為還有仗可打。
狄醒宇說:“以前擔心的鄱陽湖方向并無太大敵情……”
趙子立說:“李覺第70軍和夏楚中第79軍還有戰斗力,南昌外圍布防的歐震第4軍正處于應戰中,盧漢第1集團軍已在趕往江西的路上,在贛江以東還有吳奇偉的部隊,第74軍也已經趕到戰場。”
總之,兩人的意見是:在這種情況下,結束會戰,匆匆撤退,有點說不過去。
薛岳想了想,說:“那你們回去吧!這個撤退計劃由我自己擬定。”
關于薛岳堅持放棄南昌這件事,趙子立的分析,一是因為羅卓英是陳誠的人,當年薛落難,是羅找到陳,陳又找到蔣介石;二是因為薛岳不想叫自己的嫡系第4軍守南昌:“第4軍既是張發奎的嫡系,又是薛岳的嫡系,好像一個兼祧的兒子,兩門子都愛如至寶,怎肯放在南昌擔任風險呢?所以他要放棄南昌。”

上面是多年后趙子立的回憶,且是跟薛岳掰了(1944年長衡會戰)以后的說法,難免帶有“想當然”的意味。至于薛因跟羅卓英、陳誠的關系而遷就羅放棄南昌一條,不能說沒一點因素,但假如以為這是最主要的因素,就有點武斷了。
實際上,薛岳從一開始對南昌之戰就沒提起過精神。
薛岳覺得南昌跟長沙不一樣。南昌在戰略上有沒有價值?當然有。是不是非常大呢?至少薛岳認為要畫問號的。所以,當日軍兵臨贛江,趙子立提議將盧漢第1集團軍和王陵基第30集團軍主力拉到江西參與會戰時,他搖了搖頭,最后僅同意第1集團軍開往南昌外圍。
下一篇:玩轉青春 | 次元城茶話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