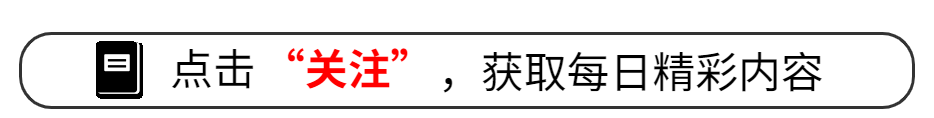陰陽失衡致災禍,風水師警告:今年家中此方位不可動土
驚蟄剛過,江南的雨就沒歇過。連綿的陰雨浸透了青磚黛瓦,連空氣里都飄著股潮濕的霉味,墻角的青苔瘋長,爬滿了半面墻。鎮子東頭的老槐樹不知怎的,竟在抽芽的時節整株枯死,黑漆漆的枝椏像鬼爪似的抓著鉛灰色的天,樹洞里積著的雨水泛著詭異的綠光,湊近了還能聞到淡淡的腥氣,引得野貓夜夜在樹下哀嚎。
鄉鄰們私下嘀咕,說這反常的天氣定是陰陽失了調和。前幾日城西李家動土蓋房,才挖了三尺深就涌出腥臭的黑水,水里還漂著碎骨似的東西,夜里更傳出孩童啼哭,那哭聲忽遠忽近,聽得人頭皮發麻,嚇得匠人連夜卷了鋪蓋逃走。更奇的是,李家門前的石獅子眼窩竟滲出水珠,如同落淚一般,擦去又會立刻滲出,石座上還凝著層薄薄的白霜。

這般異狀讓鎮民們人心惶惶,紛紛揣著米糧去求鎮上唯一的風水先生。那青磚小院的朱漆門扉緊閉,門環上的銅銹在雨霧里泛著冷光,檐角懸掛的銅鈴無風自鳴,叮咚聲里藏著能定奪禍福的玄機,引著眾人在雨巷里踮腳張望,沒人敢貿然叩門,生怕驚擾了先生修行,有人悄悄在門前放下油紙包著的糕點,轉身便匆匆離去。
丹晨子推開窗時,雨絲正斜斜地打在雕花木欞上。他束著簡單的青布發帶,素色道袍的袖口沾著些許墨痕,指尖還殘留著朱砂的溫熱。案幾上攤開的羅盤是師門所傳,黃銅盤面刻著二十八星宿,指針微微顫動,似在預警什么,盤面邊緣的云紋因常年摩挲已十分光滑,中央的天池水清澈如鏡。
窗外的石榴樹落了片枯葉,恰好飄在窗臺上。丹晨子拾起葉片,脈絡間竟泛著淡淡的黑氣。他輕捻指尖,想起師父臨終前的叮囑:“太歲當頭坐,無喜恐有禍,東南動土時,陰陽必交錯。” 今年恰逢太歲在東南,果然異象頻發,師父當年封印的陰煞之地怕是要出事,那處封印的桃木釘不知是否還穩固。
案幾左側堆著幾本線裝古籍,《宅經》《葬書》的封皮已泛黃,夾在其中的幾張符紙露出邊角,朱砂色澤鮮亮。墻角的銅爐燃著沉香,青煙裊裊上升,在梁間繞出淡淡的弧線,驅散了雨霧帶來的濕寒,屋里彌漫著沉靜的香氣。
“先生,您看這雨還要下到何時?” 門外傳來王掌柜的聲音,帶著幾分焦急。此人經營著鎮上最大的糧鋪,近來倉庫頻頻漏水,損失不小,說話時還不住地搓著潮濕的手,指縫里還沾著谷糠,青布長衫的下擺沾滿了泥點。
丹晨子轉過身,目光落在來人潮濕的鞋履上。“王掌柜鞋底沾著西坡的紅泥,想必是從那邊繞路過來的。” 他聲音溫潤,卻帶著不容置疑的沉穩,“東南角的排水溝堵了三日,淤泥積了半尺,昨日后廚的花貓叼著死鼠往那邊去,被臭氣熏得直打噴嚏,該清了,晚了恐生蠅蟲。”
王掌柜驚得后退半步,這等瑣事他從未對人說起。丹晨子卻已移步到案前,提筆在黃紙上畫了道符,筆尖劃過紙面發出沙沙聲響,朱砂在紙上暈開,形成流暢的線條:“貼在倉庫主梁東側,三日后雨停。只是切記,莫要在院中打井,那處地氣與你八字相沖,恐招水患。”

“為何?” 王掌柜接過符紙,指尖微微發顫。他家院子東南角確實低洼,正打算晴后鑿井,連工匠都已找好,昨日還特意買了新的井繩,是結實的麻繩,浸過桐油防水。
“你家宅基屬坤位,對應地母,今年太歲在東南屬巽位,主風。” 丹晨子指尖點過羅盤上的刻度,銅針突然劇烈跳動,發出細微的嗡鳴,“地遇狂風必失穩,此時動土如同捅破天機,井水會變臭,糧倉必遭鼠患,屆時囤的新米都會生蟲發霉,那損失可就大了。”
王掌柜連連點頭,將符紙小心翼翼地折好揣進懷里,又從袖中摸出個小小的錦盒:“這是家母珍藏的陳年普洱,先生莫嫌微薄。” 丹晨子接過錦盒,指尖觸到盒面的雕花,溫潤如玉,便知是上好的物件,卻也沒有推辭,鄉鄰的心意不便拂逆。
正說著,院外傳來孩童嬉鬧聲。兩個半大的孩子踩著水洼跑過,濺起的泥水弄臟了門前的石階。丹晨子望著他們遠去的背影,眉頭微蹙 —— 那方位正是鎮子的東南方,孩子們脖頸上掛的護身符竟在雨中泛著黑氣,絲線都已變得暗沉,其中一個孩子的護身符線繩眼看就要斷裂。
他取來三枚銅錢,在掌心輕搖后擲于案上,得 “澤風大過” 卦。六爻之中四陰二陽,陰盛陽衰之兆明顯。丹晨子輕嘆一聲,從藥箱里取出艾草,在香爐里點燃,裊裊青煙中帶著清苦的香氣,才壓下羅盤的異動,銅針漸漸歸于平穩,天池水也恢復了平靜。
藥箱里整齊地碼著各式符咒,黃紙朱砂、桃木小劍、糯米布袋,還有幾瓶用瓷瓶裝著的雄雞血,瓶身上貼著標簽,注明了采集的時辰,皆是陽氣最盛之時所取,效力更佳。箱底壓著一本牛皮封面的冊子,記載著鎮上各家宅基的方位與風水格局。
暮色漸濃時,藥鋪的張娘子匆匆趕來。她兒子近日夜夜啼哭,請來的郎中都束手無策,眼下眼眶紅腫,鬢邊還沾著雨珠,顯然是急壞了,衣襟上還別著兒子畫的歪扭小人,邊角已被雨水浸濕,墨跡暈開成一片模糊的藍。
丹晨子見她衣襟沾著草屑,便知她是從后門小徑跑過來的。兩人穿過濕漉漉的巷弄,沿途看到不少人家門口掛著避邪的桃枝,卻都歪歪斜斜地指向東南。有戶人家的雞籠塌了,老母雞領著雛雞在雨里亂竄,偏偏不肯往東南方向去,反倒扎堆擠在西北角的柴垛下,瑟瑟發抖。

路過鐵匠鋪時,聽見里面傳來叮叮當當的打鐵聲,火星從門縫里竄出,映紅了門前的積水。鐵匠老李光著膀子揮錘,汗水混著雨水順著脊梁流下,他打造的犁鏵本是鎮上最好的,近來卻總在淬火時開裂,試了幾次都不成,正懊惱地捶著鐵砧。
“上月是不是動過臥房的家具?” 剛進院門,丹晨子便開口問道。院中那棵石榴樹長得正旺,卻在東南枝椏處有片枯葉,與周遭生機格格不入,樹皮上還凝結著細小的水珠,如同淚珠,用手一碰便化作寒氣滲入掌心,凍得指尖發麻。
張娘子連連點頭:“是挪了個衣柜,想著給孩子騰些地方放木馬。那衣柜是孩子外婆留下的,說是紫檀木的,我想著放在窗邊能曬到太陽,哪承想自那以后孩子就夜夜哭鬧,哄都哄不住。” 她引著丹晨子進屋,臥房里果然在東南角多了個深色衣柜,將窗戶擋去大半,墻角已滲出霉斑,形狀如同孩童手掌。
丹晨子取出隨身攜帶的銅錢,三枚銅錢在掌心輕搖后擲于地面,竟是罕見的三陰卦象。他俯身細看,地板縫隙里滲著淡淡的霉斑,像極了凝固的血跡,用指尖一抹,觸感冰涼刺骨,比別處的地面要低上半分寒意,顯然陰氣聚集于此。
“今夜子時,將衣柜挪回原位。” 他從袖中取出一小包朱砂,里面還混著曬干的艾草和雄雞血粉,“用雄雞血調和,在窗欞上畫個‘鎮’字。切記,挪動時不可讓鐵器著地,要用桃木扁擔抬移,途中莫讓女子觸碰,陽氣弱的人容易被陰氣侵擾。”
張娘子喏喏應下,從袖中摸出碎銀遞上,卻被丹晨子婉拒。“災禍未除,談何酬勞。” 他望著窗外越下越大的雨,屋檐水流如簾,打在青石板上噼啪作響,“這雨再不停,鎮上恐有更大的麻煩,東南方的陰氣已聚成霧了,昨夜我觀天象,斗柄已偏向巽位,主風雨不調。”
離開張娘子家時,雨勢又大了幾分。丹晨子撐起油紙傘,傘面繪著八卦圖案,雨水順著傘沿流下,形成一道水幕。路過河邊時,見幾個婦人在燒紙,火光在雨中明明滅滅,紙錢飄落在水面上,打著旋往下游漂去,正是東南方向,婦人的哭聲被雨聲吞沒,格外凄涼。
回到自家小院時,雨勢已如瓢潑。丹晨子推開房門,只見羅盤上的指針瘋了似的轉動,最終死死指向東南方,銅針末端竟滲出細密的水珠,順著盤面紋路流淌,仿佛在泣血示警,映得他臉色凝重如鐵。他連忙取來鎮盤的玉佩,放在羅盤中央,才稍稍穩住局勢。

他取來筆墨,在紙上快速繪制鎮子的地形圖。東南方位正是鎮外那片待開發的荒地,近日有鄉紳牽頭要在此處修建祠堂,據說要請州府的官員題字,連石料都已從山里運來,堆在路邊蓋著油布,露出的邊角青黑發亮,是上好的花崗巖。筆尖在圖紙上停頓,墨滴暈開,像朵不祥的烏云籠罩在那片土地上。
墻上掛著一幅水墨山水畫,畫的是鎮上的全貌,山巒起伏,河流蜿蜒,東南方的荒地用淡墨勾勒,旁邊題著小字 “陰陽極變之處”,是師父當年所畫,提醒后人此處風水兇險。畫軸有些陳舊,邊角微微卷起,用銅軸固定著,擦拭得干干凈凈。
忽聞院外傳來急促的叩門聲,伴隨著風雨聲格外刺耳。丹晨子開門,見是里正帶著幾個鄉紳,個個面色凝重,衣袍都被雨水打濕,其中劉鄉紳的胡須還滴著水,手里拄著的拐杖底端都已泡漲,顯然是冒雨趕來,鞋上的泥點足有銅錢大小。
為首的劉鄉紳不等落座,便直截了當地說:“丹先生,祠堂地基明日就要動工,特來請您擇個吉時,最好能請您親自去現場看看,給些指點,事成之后定有厚禮相贈。” 他身后的鄉紳們紛紛點頭,眼神里卻藏著幾分不以為然,有人還在偷偷打量屋內的陳設,目光落在墻上的古畫上。
丹晨子將地形圖推到他們面前,指尖點在東南荒地的位置:“此地萬萬動不得。” 他聲音不高,卻讓喧鬧的雨聲都仿佛靜止片刻,“今年陰陽失調,東南屬巽位,主風災水患,地氣已亂如麻線,動土便是引火燒身,恐傷及鎮上百姓。”
劉鄉紳顯然不悅,捻著胡須冷笑道:“先生是怕擔責任吧?我們已請過州府的風水高人看過,說此處龍脈匯聚,是塊寶地,還畫了圖紙呢,人家可是得過御賜牌匾的,比不得我們鄉野村夫。” 他從袖中掏出張泛黃的圖紙,上面蓋著官府的朱印,邊角卻已磨損發黑,墨跡有些模糊。
丹晨子接過圖紙細看,上面的風水布局確實精妙,依山傍水,藏風聚氣,卻刻意避開了今年的太歲方位,連標注的水源走向都與實際地貌不符,顯然是刻意篡改過的。他抬頭看向眾人,目光銳利如刀:“那高人可曾說過,去年此處淹死過三個孩童?尸骨未寒,怨氣未散啊,他們的爹娘至今還在河邊燒紙,夜夜以淚洗面。”
眾人皆驚,此事因涉及鄉紳子弟,一直被壓著未曾外傳。劉鄉紳的臉色瞬間變得煞白,眼神躲閃,卻強裝鎮定:“不過是意外落水,與風水何干?先生莫要危言聳聽。” 他的手指不自覺地握緊了拐杖,指節發白。
丹晨子將圖紙揉作一團:“怨氣未散,又逢陰陽失衡,強行動土只會引災上身,到時候祠堂變兇宅,悔之晚矣。” 他的聲音在雨聲里格外清晰,帶著金石般的重量,“那高人若真有本事,為何不提及此處的暗河?暗河之上陰氣重,動土即破局。”
里正面露難色:“可木料工匠都已齊備,磚瓦堆了半畝地,若是停工,損失可不小啊,光是定金就付了五十兩銀子,都是各家湊的血汗錢。” 話未說完,便被窗外一聲驚雷打斷,院中的那棵老梅樹竟被劈斷枝干,斷口焦黑,恰好指向東南,青煙裊裊升起,帶著焦糊的氣味,眾人皆是一驚,面面相覷。

眾人望著斷折的梅枝,臉色煞白。劉鄉紳雖心有不甘,卻也被天雷劈樹的異象驚住,喏喏地應下暫停動工。丹晨子囑咐他們務必守好荒地,派專人看守,莫讓閑人靠近,尤其不可動土分毫,連草都不能拔。送走眾人,他回到屋內,卻見羅盤已裂成蛛網,東南方位的刻度徹底碎裂,窗外風雨更急,隱約傳來地動般的轟鳴,地皮都在微微震顫。那不顧警告偷偷動工的人,會引來怎樣的滔天災禍?這陰陽失衡的亂局,真能憑一紙空言徹底平息嗎?
子夜時分,雨勢稍歇。丹晨子披上蓑衣,腰間別著桃木劍,劍鞘上纏著朱砂畫的符咒,還掛著個裝著糯米的布囊,布囊邊角繡著八卦圖案。他推開院門,檐角銅鈴突然急促作響,叮咚聲里帶著尖銳的警示意味,與往日的清脆截然不同,像是在發出最后的警告。
街角的狗開始狂吠,卻都朝著東南方向,聲音里滿是恐懼,夾著嗚咽般的哀鳴,有幾只狗夾著尾巴跑回家,鉆進狗窩不敢出來。只有鎮口的老黃狗還在堅守,對著東南方齜牙咧嘴,毛發倒豎,喉嚨里發出低沉的咆哮,最終卻被一聲驚雷嚇得縮回了窩。
月色透過云層灑下,將大地照得一片慘白。沿途的草木都朝著東南方向傾斜,仿佛被無形的力量拉扯,葉片背面泛著青光,用手觸摸能感到刺骨的寒意,草葉上的露水落在手上,瞬間便化作冰粒。路邊的荊棘扭曲纏繞,形狀如同鬼爪,攔住去路,需用桃木劍撥開才能前行。
路過土地廟時,見廟門大開,里面的神像被推倒在地,香爐翻倒,香灰撒了一地,混著泥水變成灰色的漿糊。神像的臉被涂得漆黑,嘴角被畫得歪斜,透著詭異的笑容,顯然是有人在此胡鬧,丹晨子嘆了口氣,扶起神像,抹去臉上的污穢,心中暗道不好,土地爺都鎮不住這邪氣了。
剛到荒地邊緣,就聞到一股刺鼻的腥氣,混雜著泥土的腐味格外難聞。幾只夜鳥驚飛而起,翅膀拍打的聲音在寂靜的夜里格外清晰,羽毛都帶著濕漉漉的寒氣,飛了沒多遠便墜落在地,抽搐幾下便不動了,眼睛圓睜,充滿恐懼。
借著月光,他看到地面已有多處塌陷,裂縫中滲出暗紅色的泥水,在低洼處匯聚成一個個小水洼,倒映著扭曲的月影,像無數只眼睛在黑暗中眨動。泥土里混雜著白色的骨頭渣,不知是何種動物的遺骸,踩在腳下軟綿綿的,發出令人牙酸的聲響。

“果然動手了。” 丹晨子眉頭緊鎖,不遠處的地基處有明顯的挖掘痕跡,嶄新的工具散落在旁,鐵鏟上還沾著帶血的泥土,閃著詭異的紅光。有個竹籃翻倒在地,里面的饅頭已被泥水浸泡,上面還留著牙印,顯然有人在此處吃過宵夜,旁邊還扔著個空酒壺,散發著劣質燒酒的氣味,壺口爬著幾只黑色的蟲子。
他快步上前,只見地基中央有個丈許深的土坑,坑壁上布滿抓撓的痕跡,像是有什么東西曾試圖爬出,泥土里還夾雜著幾縷黑色的毛發,堅韌如鐵絲,用火折子一燎便發出焦臭的氣味,冒出黑色的濃煙,燒過的地方留下油亮的痕跡,如同瀝青。
坑邊的木樁上纏著的紅布已被撕碎,飄落在泥水里打著旋,如同凝固的血跡。木樁上刻著的 “奠基大吉” 四個字被涂抹得模糊不清,上面釘著的銅錢也已發黑,失去了金屬的光澤,輕輕一碰便碎裂開來,化作粉末。
坑底積著渾濁的雨水,水面漂浮著幾張黃紙,正是他之前畫給鄉鄰的鎮宅符。丹晨子俯身細看,符紙邊緣都已發黑,上面的朱砂符咒竟變成了暗紅色,如同干涸的血跡,顯然是被陰氣侵蝕殆盡,符咒的靈力已蕩然無存,黃紙一觸即碎,化作紙灰飄散。
他取出備用的羅盤湊近,指針瘋狂轉動,發出刺耳的嗡鳴,銅制盤面迅速蒙上一層白霜,觸手冰涼,寒氣刺骨。突然 “咔” 的一聲輕響,指針斷裂開來,斷口處冒出細小的黑煙,散發出金屬灼燒的氣味,盤面的刻度開始剝落,露出底下的黑色紋路,如同血管般蔓延。丹晨子心頭一沉,這是大兇之兆,地氣已被徹底攪亂,陰陽之氣正在瘋狂沖撞。
突然,地面劇烈震動,土坑中涌起巨大的水花,伴隨著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吼。水花濺起丈高,落在草葉上瞬間凍結成冰,發出清脆的碎裂聲,冰面上映出扭曲的影子。丹晨子連忙后退,只見水中鉆出一條水桶粗的黑影,鱗片在月光下泛著青光,頭頂還長著小小的犄角,竟是條修煉多年的陰蛟!
陰蛟擺動身軀,掀起滔天泥水,腥臭的氣息撲面而來,中人欲嘔。它的眼睛是渾濁的黃色,瞳孔豎立如蛇,死死盯著丹晨子,眼底翻涌著怨毒的紅光。巨尾一拍,旁邊的木樁應聲斷裂,木屑飛濺中,它張開巨口,露出尖利的獠牙,口中噴出的寒氣讓周圍的雨水都凝成了冰粒,打在臉上生疼,如同針扎。

丹晨子迅速從袖中取出桃木劍,劍尖蘸著隨身攜帶的朱砂,口中念念有詞:“天地玄宗,萬炁本根。廣修億劫,證吾神通。三界內外,惟道獨尊。體有金光,覆映吾身。” 口訣聲中,桃木劍散發出淡淡的金光,如同流動的火焰,逼得陰蛟不敢靠近,發出憤怒的咆哮,震得周圍樹葉簌簌落下,地面的裂縫又擴大了幾分。
“去年淹死的孩童,就是被你所害吧?” 丹晨子厲聲喝問,目光如炬。他看到陰蛟脖頸處有塊鱗片脫落,露出的皮肉上竟有個小小的牙印,想必是孩童臨死前咬下的,傷口處還在滲出黑色的粘液,滴落在地上,將泥土腐蝕出一個個小坑,冒著氣泡。
陰蛟似乎被說中痛處,猛地向他撲來,腥臭的涎水滴落地面,將青草腐蝕成黑色,冒出陣陣白煙。丹晨子側身避開,桃木劍順勢劃過蛟身,留下一道焦黑的傷痕,黑氣從傷口冒出,發出滋滋的聲響,陰蛟痛得翻騰起來,攪得泥水四濺,如同開了鍋。
丹晨子側身避開,桃木劍順勢劃過蛟身,留下一道焦黑的傷痕。陰蛟吃痛,轉身甩尾,帶起的泥水如鞭子般抽來,夾著碎石和斷木。他一個翻滾躲開,泥水落在身后的樹干上,竟將碗口粗的樹干擊出個大洞,木屑紛飛,樹干應聲傾斜,砸在地上發出巨響,驚起更多夜鳥,如同黑云般掠過頭頂。
搏斗間,丹晨子發現陰蛟的攻擊總圍繞著土坑,顯然此地是它的巢穴。他恍然大悟,這東南方位本是陰陽交匯之處,地下有條暗河,河床藏著千年陰煞,今年陰陽失衡,陰氣聚集在河床之上,加上動土驚擾,才讓這修煉多年的陰蛟破地而出,借地動之勢興風作浪,吸納陰氣壯大自身,那幾個孩童便是被它拖入暗河當了祭品。
“劉鄉紳在哪?” 丹晨子一邊與陰蛟周旋,一邊高聲問道。桃木劍雖能傷它,卻無法致命,必須找到根源所在才能徹底鎮壓。話音剛落,就見不遠處傳來呼救聲,幾個鄉紳被泥水困住,劉鄉紳更是被陰蛟的尾巴掃中,倒在地上動彈不得,腿上已滲出鮮血,染紅了身下的泥土,臉色慘白如紙,嘴唇哆嗦著說不出話。
丹晨子心頭一緊,瞥見劉鄉紳身邊散落著幾張圖紙,正是那州府高人所畫的布局圖,上面用朱筆圈著 “引龍入穴” 四個字,墨跡還未干透,卻不知這所謂的龍脈,竟是陰蛟的巢穴,那高人怕是早就知道此地兇險,故意設下的圈套,想借陰蛟出世霍亂一方,再假意收服騙取錢財。

陰蛟再次撲來,巨口張開,露出兩排尖利的牙齒,腥臭的氣息幾乎讓人窒息,帶著濃烈的腐味,如同陳年的尸臭。丹晨子深吸一口氣,屏氣凝神,桃木劍在手中挽出劍花,金光更盛,迎著陰蛟的巨口刺去,劍風凌厲,劃破了空氣。
他迅速后退,繞到土坑另一側。桃木劍雖能暫時壓制陰蛟,卻無法將其徹底制服。他環顧四周,看到不遠處有堆準備建房的青磚,每塊磚上都刻著 “平安” 二字,是鄉紳們特意訂制的,還蘸過朱砂開光,在月光下泛著淡淡的紅光。頓時有了主意,這陽剛的建材或許能鎮住陰氣,阻斷陰蛟的靈力來源。
“大家快搬磚塊,堵住土坑!” 他高聲喊道,同時用桃木劍引誘陰蛟轉向,劍鋒劃過空氣帶起金色的弧線,如同流星。劉鄉紳身邊的幾個隨從立刻行動起來,抱起青磚往坑里扔,泥水飛濺中,陰蛟的嘶吼越來越弱,卻也更加狂暴,尾巴拍打著地面,震得泥土飛濺,形成一道道土柱,如同噴泉。
丹晨子看準時機,縱身躍起,桃木劍直指陰蛟七寸。那處鱗片最薄,隱約能看到里面跳動的黑色血肉,是它陰氣匯聚之處。陰蛟察覺危險,猛地轉身,尾巴掃向他的腰側,帶著呼嘯的風聲,力量之大仿佛能掃斷山岳。他在空中扭身避開,劍尖擦著蛟身刺入土坑,頓時金光迸發,如同小太陽般耀眼,逼得眾人紛紛閉眼,連月光都為之失色。
“快撒糯米!” 丹晨子大喊著,從懷中掏出早已準備好的糯米袋,用力扔向鄉紳們。鄉紳們連忙解開帶來的糧袋,白花花的糯米撒入坑中,遇到泥水立刻冒泡,發出滋滋的聲響,冒出白色的煙霧,空氣中彌漫著焦糊的氣味,那是陰氣被糯米壓制的跡象,陰蛟在坑中痛苦地翻滾,鱗片大片脫落,露出底下血肉模糊的軀體。
陰蛟在坑中瘋狂扭動,身體逐漸被糯米和磚塊困住,鱗片紛紛脫落,露出底下腥臭的皮肉,黑色的血液流淌出來,腐蝕著磚塊,發出滋滋的聲響。丹晨子趁機跳上坑邊,將桃木劍狠狠插入坑中,劍尖沒柄而入,直達地底暗河。金光從地下迸發,陰蛟發出一聲凄厲的慘叫,聲音刺破夜空,震得周圍樹木落葉紛飛,連月色都為之暗淡,最終沉入坑底不再動彈,水面漸漸平靜下來,只余下冒著白泡的泥漿。

天快亮時,土坑終于被徹底填平。丹晨子又取來大量糯米和朱砂,混合后撒在上面,形成一個巨大的八卦圖案,線條清晰,棱角分明,再用七張符咒按北斗七星的方位封蓋,每張符咒都用桃木釘釘住,防止陰氣外泄,桃木釘深入地下三尺,確保穩固。做完這一切,他已是精疲力竭,癱坐在地望著東方泛起的魚肚白,雨水沖刷過的天空格外清澈,第一縷陽光正從東南方向透出,帶著溫暖的金色,驅散了濃重的陰氣。
劉鄉紳拄著拐杖走上前,滿臉羞愧:“丹先生,都怪我固執己見,輕信那江湖騙子,差點釀成大禍,連累了鎮上百姓。” 他身后的鄉紳們也紛紛致歉,有人已在收拾工具,承諾會將地基恢復原狀,永不在此動土,還愿意賠償鎮上因此造成的損失,有人拿出銀兩,有人送來糧食,場面十分誠懇。
丹晨子擺擺手,聲音因疲憊有些沙啞:“非你之過,是陰陽失衡所致,也是天數使然。” 他望向初升的朝陽,陽光灑在東南方的土地上,泛起溫暖的金光,驅散了最后的陰霾,“今年太歲在東南,地氣紊亂,任何動土都會引發災禍。待明年太歲移位,陰陽調和,地氣歸位,方可再議修建之事,屆時需重新勘察風水,另擇吉地。”
他撿起地上的破碎圖紙,上面的 “引龍入穴” 四字已被泥水浸透,變得模糊不清,墨跡暈開如鬼畫符。“那州府高人早已卷款而逃,他豈會不知此處是陰蛟巢穴,不過是借你們之手破開封印,好讓陰蛟出世為禍,他便能趁機收取驅邪費用,此等用心險惡至極,日后需多加提防此類江湖術士。” 丹晨子將圖紙撕碎,隨風飄散,紙屑落地瞬間便被朝陽曬干,化作飛灰。
消息傳回鎮上,百姓們紛紛拆除了東南方位的建筑,將挪位的家具復原。張娘子的兒子不再啼哭,夜里還能笑著說夢話,夢見滿地桃花;王掌柜的糧倉不再漏水,老鼠也銷聲匿跡,囤的新米顆粒飽滿,散發著清香。說來也奇,自那日后,連綿的陰雨終于停歇,陽光普照大地,鎮子又恢復了往日的生機,連東頭枯死的老槐樹都抽出了嫩芽,嫩綠的葉片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市集重新熱鬧起來,攤販們的吆喝聲此起彼伏,賣早點的鋪子飄出誘人的香氣,熱氣騰騰的包子饅頭剛出籠,便被搶購一空。孩子們在巷子里追逐嬉戲,脖頸上的護身符重新煥發光澤,絲線變得鮮亮,笑聲清脆悅耳,充滿了活力。

丹晨子站在自家院中,看著修復好的羅盤,指針穩穩指向正南方,再無絲毫顫動,盤面的光澤也恢復了溫潤。他將斷裂的舊羅盤收好,埋在院角的石榴樹下,上面覆蓋著艾草和朱砂,用青石壓住,防止陰氣侵蝕,石榴樹的枝葉更顯繁茂,葉片翠綠欲滴。
他知道,這場因陰陽失衡引發的災禍雖已平息,但風水之道,在于順應自然,而非強行改變。就像這東南方位的土地,需待太歲移位,陰氣散盡,方能再動,急功近利只會適得其反。天地間的陰陽平衡,容不得半點強求,正如師父所言:“順天者昌,逆天者亡,風水不是改命的利器,而是順應天道的指引,需心懷敬畏,方能長治久安。”
這場由陰陽失衡引發的風波,終在丹晨子的智慧與勇氣下平息。它讓人們明白,風水并非虛無縹緲的玄學,而是對自然規律的敬畏與順應,是古人在千百年生活中總結的生存智慧,蘊含著對天地萬物的深刻理解。東南方位的警示,不僅是對動土的禁令,更是對天地法則的尊重,提醒世人不可妄自尊大,違背自然規律終將自食惡果。
陰陽調和,萬物方能共生;順應自然,災禍自會遠離。丹晨子用他的行動詮釋了風水的真諦 —— 不是逆天改命,而是順勢而為,在天地規則中尋求平衡,以敬畏之心對待世間萬物。那片東南荒地后來種上了桃樹,每年春天繁花似錦,鎮民們路過時都會駐足片刻,想起那場驚心動魄的較量,也銘記著陰陽平衡的道理,將這份敬畏代代相傳。

這個古老的鎮子在經歷動蕩后,更懂得與自然和諧共處的重要性。屋檐的銅鈴依舊在風中輕響,卻不再預警災禍,而是吟唱著生生不息的歌謠,清脆悅耳。市集恢復了往日的喧囂,孩子們的嬉笑聲充滿街巷,河邊的婦人不再哭泣,取而代之的是洗衣時的歡聲笑語。
這份對天地的敬畏之心,如同羅盤上的指針,永遠指引著人們在陰陽平衡中尋求安寧,在歲月流轉中代代相傳,護佑著一方水土的平安喜樂。古鎮的炊煙在晨光中升起,與朝霞融為一體,風水流轉,陰陽調和,讓這片土地的煙火氣在順應天道中綿延不絕,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