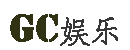從小到大 我都和鐘司渡綁在一起 幼時(shí)是他的保姆 該讀書(shū)時(shí)被送去瀛城
《魚(yú)米翻山》
從小到大,我都和鐘司渡綁在一起。
幼時(shí)是鐘司渡的保姆玩伴。
該讀書(shū)時(shí)被送去瀛城,不學(xué)文化課,只學(xué)如何侍奉丈夫。
十八歲,我被鐘太太帶回港城。
因?yàn)樗⒉环判溺娝径沙鋈y來(lái),要我回來(lái)替他紓解。
我都做得很好。
直到那晚,他摟著我喊「楠楠」。
我笑了,溫柔地替他整理領(lǐng)帶:
「娶回來(lái)吧,我不介意。」
他欣喜若狂,沒(méi)看見(jiàn)我藏在袖口的機(jī)票。
我是說(shuō)不介意。
但我沒(méi)說(shuō),我不會(huì)離開(kāi)。

入夜。
我被突如其來(lái)的光亮晃醒。
蓋著的被子被拽開(kāi),我下意識(shí)坐直身。
門(mén)外帶來(lái)的涼氣霎時(shí)間竄進(jìn)我的睡衣里。
說(shuō)是為了早些為鐘家開(kāi)枝散葉,鐘太太為我準(zhǔn)備的睡衣都格外清涼。
在我失神之際,鐘司渡扯落了我的睡袍。
一個(gè)用力,我便被摜到床頭。
絲絲縷縷的長(zhǎng)發(fā)拂過(guò)鐘司渡滾動(dòng)的喉結(jié),跟著慣性落回時(shí)堪堪擋住了乍泄的春光。
男人一手扣在我腰間,另一只手撫順了礙事的長(zhǎng)發(fā):
「在瀛城都學(xué)什么了,演示給我看看?」
我咬著唇,慌忙跪坐下來(lái)替他解扣子。
金屬扣子冰涼,像是和我作對(duì)一般不聽(tīng)話。
良久,鐘司渡終于沒(méi)了耐心,一手扣在我腰間,另一只手不輕不重地擦過(guò)我耳垂。
他的鼻尖埋入我頸側(cè),而后狠狠張嘴,毫不留情地咬下去。
我疼得倒抽一口冷氣,渾渾噩噩嗚咽。
不知過(guò)了多久,我越過(guò)他頭頂,看到窗外已然天亮。
最后一次狂風(fēng)暴雨驟停,鐘司渡死死抱著我。
那雙有力的手臂圈住我的腰,酒氣充斥我的鼻腔,幾乎讓我喘不過(guò)氣。
我忍著疼想替他清潔一下,卻聽(tīng)見(jiàn)他語(yǔ)氣委屈:
「楠楠,瘦了。」
我的動(dòng)作僵住。
楠楠。
我不叫楠楠。
「別不要我,好不好?」
「抱抱我,楠楠。」
「說(shuō)你想我。」
鐘司渡身上的酒氣還沒(méi)散。
我渾身發(fā)冷,直愣愣地瞧著他。
雖然從小就跟在鐘司渡身邊,可正式的訂婚宴前幾天才辦完。
不到一周的時(shí)間。
我的未婚夫就在我的床上,叫了別的女人的名字。
但我甚至沒(méi)有資格反抗。
也沒(méi)開(kāi)口問(wèn)一句。
忍著痛替他擦拭干凈以后才抱著被子在床的另一側(cè)睡下。
我死死瞪著天花板,已經(jīng)提前看到了風(fēng)雨欲來(lái)。
鐘太太這個(gè)時(shí)候接我回港城就是為了初嘗情事的鐘司渡不出去亂搞,就是為了要我替他紓解的。
但他心里有了別人,我不知道他有沒(méi)有碰過(guò)她。
思緒停在這兒,聞著空氣中的麝香甜氣,我突然開(kāi)始反胃。
想起在瀛城老師教過(guò)的「不癡不聾不做阿家翁」,惡心得更厲害了。
我往床上瞥了一眼,見(jiàn)鐘司渡仍合眸睡著,便輕手輕腳進(jìn)了浴室。
水流傾瀉而下,我閉上眼,用力去搓剛剛鐘司渡咬過(guò)的地方。
可再睜開(kāi)眼那些討厭的齒痕還是存在。
我攥著手機(jī),對(duì)面的投資人禮貌又紳士:
「想得怎么樣了?」
我咬住下唇,敲了幾行字又刪掉。
再等等吧。
他們都說(shuō)不要深夜作決定。
我先去查查,剩下的過(guò)后再說(shuō)。
做好心理建設(shè)以后,我才刻意拉開(kāi)了和鐘司渡之間的距離睡下。
夢(mèng)里,兵荒馬亂。
再有意識(shí),是一道女聲吵醒了我。
我連忙坐起來(lái),看著進(jìn)了房間捂住鼻子的鐘太太。
此時(shí),屋內(nèi)的腥氣和煙酒味道還沒(méi)有散去。
鐘司渡不知什么時(shí)候便已離開(kāi)了。
窗簾還拉著,屋內(nèi)一絲光亮也沒(méi)有。
她不耐煩地捂著鼻子開(kāi)了燈,陰陽(yáng)怪氣:
「哪里有你這樣做媳婦的,又污糟又亂,服侍好司渡了沒(méi)?」
鐘太太向來(lái)是這樣。
她做慣了豪門(mén)主母,滿心滿肺只有他千尊萬(wàn)貴的兒子。
我跪坐在床上,手指死死攥著被角。
她身上的香水味混雜著屋里未散的氣味,熏得我直皺眉。
「見(jiàn)著我不知道喊人的呀,也不知道去瀛城學(xué)了什么。」
我低低喚了一聲,身上的被子卻一時(shí)不察,被她「不經(jīng)意間」拽掉了。
鐘太太盯著我身上的紅痕皺著眉:
「叫你回來(lái)服侍司渡,又不是要你榨干他的。」
「以后注意分寸。」
我死死咬著牙,平復(fù)那股氣勁兒。
「我是沒(méi)別的意思呀,但你不合格的,都做了司渡的未婚妻了,怎么半點(diǎn)都沒(méi)約束好他。」
「方姒呀,司渡在會(huì)所的照片都傳到我這里來(lái)嘞。」
「他好似有些飲多咗,你快去將他接回來(lái)。」
「就現(xiàn)在。」
她扔下一句話便停了對(duì)我的嘲諷,走得利索。
我盯著床頭柜上的表,嘆了口氣。
連忙洗漱干凈,化了淡妝,穿上得體合適的裙子出發(fā)。
會(huì)所走廊鋪著厚厚的地毯。
我的高跟鞋踩上去沒(méi)有發(fā)出任何聲音。
就像我這十八年。
默默無(wú)聞,連片漣漪也帶不起來(lái)。
還未到鐘太太說(shuō)的那個(gè)包廂,我便聽(tīng)到了拐角處的笑聲:
「鐘少爺說(shuō)好給咱們一直語(yǔ)音,讓咱都聽(tīng)聽(tīng)小嫂子床上的動(dòng)靜,誰(shuí)想到他真喝多了。」
「怎么說(shuō),喝多了就喝多了,能惹出什么禍?」
「鐘少爺昨晚喊楠楠名字了。」
「哎呀,好刺激。」
「方姒再軟柿子也得讓咱鐘哥給氣死。」
「哎呀你不知道,她哪敢啊。」
「人家鐘家當(dāng)童養(yǎng)媳養(yǎng)著的,她哪能對(duì)主人炸毛啊。」
「還是人家鐘阿姨會(huì),羨慕死人了。」
「昨兒我睡得早錯(cuò)過(guò)了,那鐘哥叫了楠楠名字以后方姒說(shuō)什么了?」
「我也沒(méi)聽(tīng)著,后來(lái)只能聽(tīng)到浴室水聲了,我估計(jì)是在里面悶悶地哭去了。」
……
我站在原地,指甲陷入掌心。
拐角處的聲音漸漸遠(yuǎn)了,但還是聽(tīng)得到:
「周楠那病秧子不是快死了嗎?」
「我看不像,說(shuō)是肝癌晚期,都快蹦跶兩年了。」
「鐘少不信啊,誰(shuí)勸也沒(méi)法子,喏,前天鐘少剛給她轉(zhuǎn)了五十萬(wàn)。」
原來(lái)將死之人,也能靠財(cái)富續(xù)命。
包廂門(mén)突然被打開(kāi)。
鐘司渡跌跌撞撞地跑出來(lái)。
身上的酒氣比昨夜更重。
他一手捂著胃,另一只手臂上掛著昨天我替他搭配好的外套。
我快步向前扶住他。
鐘司渡看見(jiàn)我時(shí)瞳孔狠狠一縮:
「你怎么來(lái)……」
「來(lái)接你。」
我打斷他,接過(guò)他手上的外套。
拿到外套時(shí),鐘司渡身上的香水氣鉆進(jìn)我鼻腔。
一道是他慣用的龍涎,另一道……
是很陌生的甜膩味道,還沾著點(diǎn)消毒水的氣味。
他甩開(kāi)我的手:
「阿娰,我現(xiàn)在不能和你回家。」
我的手頓住,卻還是開(kāi)口勸道:
「你胃不舒服,回去輸液吧。」
他甩開(kāi)我的手:
「我有事,別跟上來(lái)。」
我看著他跌跌撞撞往外跑,是一副為情所困的模樣。
突然忍不住開(kāi)口叫住他:
「司渡。」
「把她娶回來(lái)吧,別讓姑娘家傷心。」
鐘司渡猛地停下腳步,回頭看向我。
他眼里有震驚,有遲疑,最后變成了狂喜。
周?chē)娜烁且桓辈豢伤甲h的模樣,紛紛低聲感嘆鐘少爺有個(gè)這樣大方的未婚妻。
「阿娰,你……」
我溫柔地笑,就像在瀛城學(xué)到的那樣,溫順、體貼、毫無(wú)攻擊性。
「你放心,我不會(huì)鬧的。」
他大步走回來(lái),一把抱住我,用力在我額頭上親了一下:
「阿娰,果然還是你懂事。」
聽(tīng)見(jiàn)這話,我心下還是一滯。
那不懂事的是誰(shuí),似乎不用多說(shuō)了。
「你放心,不管怎么樣,你都是唯一的鐘夫人,她不會(huì)影響到你的地位的。」
「而且楠楠身體不好,在我們正式大婚之前,我也不會(huì)讓她生下孩子影響我們兒子的地位。」
雖有心理建設(shè),但真正聽(tīng)見(jiàn)這話時(shí),我的心臟還是像被針尖密密麻麻碾過(guò)。
齊人之福不過(guò)如此。
這就是我的婚姻。
我的全部。
丈夫心里躺著白月光,身下躺著替身新娘。
胃里翻江倒海,我卻開(kāi)始慶幸。
好在,好在去瀛城的三年并沒(méi)磨平我的性子。
我還算是一個(gè)正常的,新時(shí)代的女性。
我還會(huì)為背叛感到憤怒,感到惡心。
我還是覺(jué)得,我是個(gè)獨(dú)立的,不需要依附旁人的個(gè)體。
萬(wàn)幸。
鐘家只把我當(dāng)童養(yǎng)媳。
港城人大半不怎么在意法律上的關(guān)系,萬(wàn)幸我和鐘司渡并沒(méi)領(lǐng)證。
這些年我靠著代寫(xiě)作業(yè)和接畫(huà)稿攢了一些錢(qián)。
等到合適的時(shí)候留下一半作為鐘家養(yǎng)我到成人的報(bào)答,剩下的就作為我開(kāi)啟新生活的資金。
鐘司渡太高興。
以至于沒(méi)發(fā)現(xiàn)我手里捏著的,是回內(nèi)地的機(jī)票。
就在今晚。
鐘司渡匆匆走了。
我站在會(huì)所門(mén)口,看著他的車(chē)消失在夜色里。
手機(jī)振動(dòng),我迅速劃開(kāi),是投資人發(fā)來(lái)的信息。
【考慮好了嗎?】
我低頭打字:
【今晚就過(guò)去。】
發(fā)完,我抬頭看了看港城的夜空。
十八年了。
我不知自己的來(lái)處。
不知生母身份,更不知父親姓甚名誰(shuí)。
從我記事起,我就成為鐘司渡的附庸。
小時(shí)候周?chē)腥藢?duì)我?guī)缀醵际禽p蔑和惡語(yǔ),我當(dāng)時(shí)尚且不知緣由。
直到七歲,要被送去瀛城時(shí)我才明白。
鐘家唯一正室夫人所出的鐘司渡鐘大少爺身體不好,需要八字恰當(dāng)?shù)呐_喜。
像鐘家這般的家庭已經(jīng)不需要用聯(lián)姻來(lái)維持地位,當(dāng)然是繼承人的身體更重要。
為了給他續(xù)命,鐘家從內(nèi)地尋了我過(guò)來(lái)。
我在鐘家做狗,一做就是十八年。
好在我算「覺(jué)醒」,終于要有機(jī)會(huì),逃出這座牢籠。
回到鐘家別墅時(shí),天已經(jīng)完全黑了。
門(mén)口的保安看到我恭敬行禮:
「少夫人回來(lái)了。」
我點(diǎn)點(diǎn)頭,快步走向主樓。
這個(gè)時(shí)間鐘太太應(yīng)該正在參加慈善晚宴。
鐘司渡估計(jì)還在陪他的楠楠你儂我儂。
臥室還是我離開(kāi)時(shí)的樣子,床單凌亂,空氣中殘留著情欲的味道。
本是該保姆來(lái)收拾的,但鐘太太為了給我立規(guī)矩,說(shuō)鐘司渡的房間不能有別人進(jìn)來(lái),只能我這個(gè)少夫人親自動(dòng)手。
她總看著我跪在地下,拿著小抹布一點(diǎn)一點(diǎn)地把近一百平的臥室擦干凈。
不過(guò),以后不會(huì)再有了。
我打開(kāi)衣柜,里面掛滿了她為我準(zhǔn)備的高定,每一件都價(jià)值不菲。
也是。
她雖苛責(zé)我,在外人面前卻還是很會(huì)演戲的。
我拿出早上準(zhǔn)備好的行李箱,快速收拾行李。
衣柜底下有個(gè)暗格,我蹲下身,從里面拿出一個(gè)牛皮紙袋。
這就是在鐘家真正屬于我的東西,也算得上我的全部家當(dāng):
護(hù)照,身份證,一張鐘家人不知道的銀行卡。
卡里是除我留給鐘家那張卡以外,這三年里我偷偷攢下的錢(qián),不多,但足夠我重新開(kāi)始。
梳妝臺(tái)上的首飾盒里躺著幾件昂貴的珠寶,都是鐘太太送的。
她常去慈善拍賣(mài)會(huì),帶回了不少好東西,都送給我了。
從這個(gè)角度來(lái)說(shuō),她對(duì)我也算極好。
我一件都沒(méi)拿。
還有一個(gè)玉墜,是我小的時(shí)候鐘司渡從鐘太太那拿來(lái)送給我的。
說(shuō)這個(gè)墜子是我進(jìn)來(lái)鐘家時(shí)襁褓里藏著的,應(yīng)該是我的東西,可能和我的親生父母有關(guān)。
但我也還是沒(méi)拿——
我早就過(guò)了需要父母關(guān)愛(ài)的年紀(jì)了。
目光落在床頭柜上。
那里還擺著我和鐘司渡的訂婚照。
照片里我笑得溫婉,他摟著我的腰,眼神卻瞟向別處。
真算得上貌合神離。
虧我當(dāng)時(shí)還覺(jué)得他滿眼是我。
我拿起照片,輕輕放進(jìn)抽屜里。
其實(shí)最后真的沒(méi)什么可帶的。
我的東西很少,少到一個(gè) 24 寸的行李箱就能裝完。
不到半小時(shí),除了我留給鐘家的那張卡,這里已經(jīng)沒(méi)有任何我生活過(guò)的痕跡了。
鐘太太不在家,傭人們也不敢攔我。
我拖著箱子走到門(mén)口時(shí),管家猶豫著開(kāi)口:
「少夫人,這么晚了,您要去哪兒?」
我笑了笑,語(yǔ)氣溫馴有禮:
「去接少爺呀。他喝多了,讓我?guī)Q洗衣物去酒店。」
「需要叫司機(jī)送您嗎?」
我晃了晃車(chē)鑰匙:
「不麻煩,我自己開(kāi)車(chē)去。」
他信了,恭敬地送我出門(mén):
「少夫人路上小心。」
「好。」
車(chē)庫(kù)里的車(chē)不少,我選了最不起眼的那輛黑色奔馳。
這車(chē)總是傭人在開(kāi),不會(huì)太引人注目。
車(chē)子駛出鐘家別墅大門(mén)時(shí),我手心全是汗。
后視鏡里,管家的身影越來(lái)越小,最后消失在夜色中。
我開(kāi)了二十分鐘,最后在一個(gè)沒(méi)監(jiān)控的路邊停下。
這里離機(jī)場(chǎng)還有段距離,但已經(jīng)很安全了。
我把車(chē)鑰匙扔在后座,連車(chē)門(mén)都沒(méi)鎖,抬手?jǐn)r了一輛計(jì)程車(chē),直接去了港城機(jī)場(chǎng)。
計(jì)程車(chē)駛上高速,窗外的維多利亞港飛快掠過(guò)。
我拿出手機(jī),刪掉了所有和鐘家有關(guān)的聯(lián)系人。
相冊(cè)里那些虛偽客套的笑,聊天記錄里違心的問(wèn)候,統(tǒng)統(tǒng)消失在我的世界。
還剩最后一個(gè)「周秉君」時(shí),我猶豫了一下。
手指在刪除鍵上停頓了幾秒,最終只是取消了置頂。
去瀛城之前,不論出于什么打算,他給我塞了一張黑卡。
那是我賺錢(qián)的起點(diǎn)。
他還說(shuō)要我永遠(yuǎn)記得我只是方姒,不是任何人的附庸。
我一直記得。
我捏了捏手機(jī),最后還是沒(méi)有發(fā)消息給他。
機(jī)場(chǎng)的燈光越來(lái)越近,我付完車(chē)費(fèi)拖著行李箱走進(jìn)航站樓。
換登機(jī)牌時(shí),前臺(tái)的工作人員遞給了我一包柔巾紙:
「女士,您的眼睛有點(diǎn)紅。」
「可能是太累了。」
我笑得很勉強(qiáng)。
畢竟在港城生活這么多年,驟然離開(kāi),心里倏地空了一塊。
我不知來(lái)處。
往后所有,只能看歸途。
過(guò)安檢時(shí)我的護(hù)照被反復(fù)檢查,我心里那根弦緊繃著,生怕出現(xiàn)什么意外。
好在,最后工作人員還是蓋了章:
「祝您旅行愉快。」
我透過(guò)舷窗,最后看了一眼港城的夜色。
手機(jī)突然震動(dòng),是鐘司渡的來(lái)電。
我抬手按下關(guān)機(jī)鍵。
空姐替我將包裹放在行李架上,低頭的時(shí)候正好看到我發(fā)抖的雙手和通紅的眼。
她溫柔開(kāi)口:
「女士,您還好嗎。」
「我很好,謝謝您。」
我很好。
從來(lái),沒(méi)這么好過(guò)。
機(jī)艙門(mén)緩緩關(guān)閉。
飛機(jī)開(kāi)始滑行時(shí),我系好安全帶,閉上了眼睛。
這一次,我終于可以為自己活了。
鐘司渡推開(kāi)別墅大門(mén)的時(shí)候,腳步頓了一下。
往常這個(gè)時(shí)候,方姒都會(huì)在客廳等他。
她是個(gè)十足溫婉賢惠的夫人,等他的時(shí)候要么看書(shū),要么插畫(huà),要么洗手作羹湯。
反正全是為了他。
見(jiàn)他回來(lái),不管正在做什么,她都會(huì)立刻放下手上的事情,輕聲問(wèn)他渴不渴餓不餓,要不要吃點(diǎn)夜宵。
但今天,客廳里空蕩蕩的。
「方姒?」
他喊了一聲,沒(méi)人應(yīng)答。
鐘司渡皺了皺眉,心里是突如其來(lái)的不安。
他抬腿往樓上走。
主臥室的門(mén)半開(kāi)著,他推門(mén)進(jìn)去,發(fā)現(xiàn)衣柜的門(mén)也開(kāi)著。
方姒的衣服少了一半,只剩下那些煩瑣的禮服。
梳妝臺(tái)上,她慣用的護(hù)膚品也不在了。
床頭柜上他們剛剛拍好的訂婚照也不見(jiàn)了。
鐘司渡的心猛地一沉。
他快步走向衣帽間,拉開(kāi)方姒放證件的抽屜:
空空如也。
什么都沒(méi)有了。
他的太陽(yáng)穴突突直跳:
「潘岳良!」
他厲聲喊管家。
阿良匆匆趕來(lái),不知為什么大少爺突然發(fā)了這么大脾氣:
「少爺,您回來(lái)了。」
「少夫人呢?」
潘岳良的心怦怦跳了起來(lái)。
少夫人走的時(shí)候明明說(shuō)去接大少爺了,怎么沒(méi)跟著一起回來(lái)呢。
下一篇:從生辰八字看桃花情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