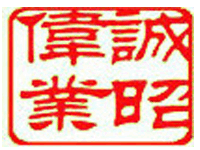《紅樓夢》解讀: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quán)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直至第十五回,《紅樓夢》的編排與結(jié)構(gòu)漸入佳境,是時(shí)候摒棄一個(gè)淺顯的認(rèn)知了——《紅樓夢》絕非僅是寶玉、黛玉與寶釵間的三角戀情。細(xì)讀至此,你是否察覺?寶釵與黛玉已多時(shí)未現(xiàn),真正鋪展的是賈府的盛景繁華。
更深一層,回溯第一、二回,有塊曾在靈河岸邊修煉的石頭,欲赴人間歷劫繁華。臨行前,與它淵源深厚的絳珠草誓愿相隨,誓要以淚水償還昔日灌溉之恩。此番下凡,不單是寶玉與黛玉,賈府中眾人亦皆同往,共赴人間,了結(jié)前世糾葛。
于是,太虛幻境中宣告:一眾前緣未了的冤孽,齊赴塵世,誓要在此生中,一一償清過往的情緣債。
在《紅樓夢》的哲學(xué)視角下,人生所遇,皆為有緣之人,其中緣分最深者,莫過于夫妻、父子、母女。第十四回末,北靜王的登場,與寶玉結(jié)下了一段奇特的緣分。北靜王久聞寶玉銜玉而生,心生好奇;寶玉亦常聞北靜王之謙和,欲圖一見。秦可卿喪禮之上,二人終得相見。北靜王問及寶玉口中含玉,寶玉便解玉以示。雖交談不過數(shù)語,卻讓人感受到二人間那份難以言喻的緣分,恰似書中開篇神話世界里所提及的玄妙之緣。
我們常常關(guān)注緣的深淺與長短,卻忽略了緣有時(shí)也是一種難解的糾纏。親子之間,雖有深緣,卻也可能相處不和,成為冤家。夫妻亦然,愛恨交織,難以割舍。《紅樓夢》中的緣,往往超越世俗邏輯,令人費(fèi)解又著迷。
而最易被忽視的,莫過于北靜王與寶玉之間那淡淡的緣分。或許只是生命中的一次擦肩,旅途中的偶然相遇,交談幾句后便各自離散,甚至未知姓名。然而奇妙的是,這樣的畫面卻常在心頭浮現(xiàn),成為生命中難以忘懷的一幕。
曾記得在泰國芭堤雅一個(gè)小島上,偶遇一位中年婦人,她失聲痛哭,周圍人群靜坐旁觀。雖不懂泰文,我仍上前安慰。這一幕,至今銘記,或許只是因緣際會(huì),讓我在那個(gè)瞬間出現(xiàn),給予她一絲慰藉。她或許也覺詫異,這位突如其來的傻大個(gè),說著她聽不懂的語言。
有時(shí),緣分就像一種微妙的心事,讓你感覺某地似曾相識(shí),某人仿佛舊友重逢。正如佛經(jīng)所言,“不受后有”,有些緣分或許僅是一面之緣,了無后續(xù)。寶玉與北靜王的相遇便是如此,相見之后,再無交集。但他們見面的那一刻,卻仿佛有著前世未了的糾葛。北靜王欲觀寶玉之玉,舉止間透露出一種莫名的前世關(guān)聯(lián)。觀后,他親自為寶玉戴好,并轉(zhuǎn)身對賈政言及富貴之家的教育之道,雖為客套,卻難掩其對寶玉的好奇。寶玉亦覺北靜王相貌非凡,此等緣分,瞬息即逝,難以言喻。
《紅樓夢》的魅力,不僅限于寶釵、黛玉與寶玉之間深厚的緣分。第十五回尤為有趣,寶玉與兩位人物的短暫交集,令人玩味。一位是尊貴無比的北靜王,另一位則是鄉(xiāng)間少女二丫頭。這些生命中的剎那緣分,雖短暫卻多姿多彩,令人回味無窮。

前世緣分的深情體悟
北靜王訪見寶玉后欲辭行,賈赦、賈政、賈珍恭敬旁立,目送其離去。北靜王謙遜有加,言及秦可卿已登仙界,人間輩分自當(dāng)不論。雖貴為王爺,亦不愿先于靈車而行,待靈車啟動(dòng)后,方緩緩離去。
然而,這場喪事卻似郊游一般,寶玉與秦鐘之行徑尤為突兀。秦鐘在其姐喪禮上,非但未顯悲痛,反而跑到廟宇中調(diào)戲尼姑智能兒,全然不顧場合。孩童們對喪事無甚感觸,即便逝去的是至親。富貴之家鮮少涉足鄉(xiāng)間,對農(nóng)具如犁等陌生不已,竟將其作為玩物擺弄。此情此景,不禁令人憶起劉姥姥初入賈府之時(shí)的懵懂,面對鐘表這一未知之物,驚懼萬分。
作者以平等之筆觸,描繪人世百態(tài),無論貧富貴賤,皆有其“不知”之處。寶玉下鄉(xiāng),與劉姥姥入府無異,皆因環(huán)境陌生而顯得無知。寶玉偶遇手搖紡紗車,心生好奇,上前嘗試,卻不慎招致一旁女子責(zé)備。隨從見狀,怒斥女子放肆,竟敢對寶玉無禮。屋內(nèi)人聞聲,急喚二丫頭前來,女子遂離去。二丫頭或?yàn)檗r(nóng)家之女,紡紗車乃其日常所用。寶玉無心之舉,或已擾亂她一日辛勞成果,故而發(fā)怒。
《紅樓夢》深探人世間生命的因果與緣分,尤其是那可知與不可知的微妙聯(lián)系。寶玉對此深有體悟,他珍視生命中每一份深淺不一的緣分。當(dāng)二丫頭搖紡車時(shí),秦鐘稱其“大有意趣”,盡顯其內(nèi)心蓬勃的欲望與輕浮。相比之下,寶玉則顯得更為教養(yǎng)有分寸,他明白此時(shí)不應(yīng)調(diào)戲這位鄉(xiāng)間少女。此情節(jié)巧妙對比了寶玉與秦鐘的情感態(tài)度,秦鐘之言行易流于低俗調(diào)戲,而寶玉則在未見二丫頭時(shí)感到一絲惆悵,此情非占有,僅為似曾相識(shí)之感,緣淺而令他哀傷。
寶玉之“情”復(fù)雜而深刻,他深情而不濫情,若無秦鐘之對比,或許難以察覺。當(dāng)夜,秦鐘沉溺于與尼姑智能兒的欲望之中,寶玉卻前來阻止。此情此景,更顯秦鐘之放縱與寶玉之灑脫。寶玉與北靜王、二丫頭的交談,皆流露出對前世緣分的深情體悟。他之情,非簡單欲望所能概括,而是對人與人之間微妙聯(lián)系的深刻體悟與重視。
細(xì)讀《紅樓夢》,北靜王與寶玉的相會(huì)雖淡,卻余韻悠長。初讀時(shí)或許易忽略,但近年來,我愈發(fā)感到這一人物的獨(dú)特魅力。他與寶玉之間,似有一種超脫塵世的純凈之緣,清淡如水,無牽無掛,僅當(dāng)下相遇,無后續(xù)糾葛,這份緣分異常清凈。
二丫頭亦是如此。寶玉尊貴之軀踏入農(nóng)家,二丫頭并未將其視為特殊,甚至因他亂動(dòng)?xùn)|西而訓(xùn)斥。在秦可卿出殯之日,寶玉邂逅了兩位難忘之人:北靜王與二丫頭。二人身份、性別迥異,卻與寶玉有著深厚的情感紐帶。
觀北靜王,寶玉舉目所見,乃是一位頭戴潔白簪纓銀翅王帽,身著江牙海水五爪坐龍白蟒袍,腰系碧玉紅鞓帶的秀麗人物。水溶,北靜王之名,其帽插銀翅,袍飾江牙海水,彰顯其開國四大王爺之一的高貴身份。鞓,今已少用,實(shí)為紅色皮帶。北靜王膚色白皙如玉,眼眸明亮如星,真乃人中龍鳳。
在《紅樓夢》中,對出場人物的細(xì)致描繪往往意味著其非凡身份,寶玉的凝視便是在辨認(rèn)前世的緣分。小說開篇的神話便講述了天上擁有仙緣之人紛紛下凡,他們在人間自然都是風(fēng)貌出眾,因他們身上承載著前世的仙機(jī)。
寶玉與北靜王的相遇便是如此。寶玉搶步上前參見,而北靜王則從轎內(nèi)伸手挽住他,阻止他下跪,這是他們最親密的接觸。隨后,北靜王也仔細(xì)打量了寶玉,發(fā)現(xiàn)他同樣裝扮華麗,面容姣好。值得注意的是,兩人的著裝都以銀白色為主,僅皮帶為紅色,顯得格外清新脫俗。這不僅僅是對色彩的敏感把握,更寓意著他們之間緣分的純凈無瑕。
寶玉的穿著時(shí)常變換,但這一天他選擇了與北靜王相似的白蟒箭袖,使得兩人在外貌上更加相像。讀來不禁讓人遐想,仿佛北靜王是寶玉某個(gè)前世緣分的轉(zhuǎn)世,他們之間有著難以言喻的親近感。這種親近并非糾纏,而是同一種生命狀態(tài)的體現(xiàn),宛如孿生兄弟。
當(dāng)北靜王稱贊寶玉“名不虛傳,果然如‘寶’似‘玉’”時(shí),我們不難感受到他多年來一直期待著能遇到一個(gè)與自己品貌相當(dāng)?shù)娜恕_@種期待并不容易被察覺,因?yàn)橐坏┫萑氍F(xiàn)實(shí)的糾葛中,即使是再出眾的品貌也可能被玷污。寶玉與北靜王的會(huì)面卻如同一股清流,保持著那份難得的純凈與高雅。在《紅樓夢》中,許多人物都在尋找生命中的知己,而寶玉與北靜王的相遇無疑是對這種知己之情的完美詮釋。

北靜王“鹡鸰”念珠贈(zèng)寶玉
北靜王對寶玉的玉表現(xiàn)出濃厚興趣,問道:“銜的那寶貝在哪里?”寶玉連忙從內(nèi)衣中取出,遞給了北靜王。這一舉動(dòng)無疑拉近了兩人的距離,寶玉將帶有自己體溫的玉交給北靜王,顯得尤為親近。
北靜王細(xì)細(xì)觀賞,念出玉上的字,好奇地問:“果真靈驗(yàn)嗎?”賈政忙回應(yīng):“雖如此說,但未曾試過。”北靜王對這塊玉贊不絕口,親自為寶玉理好彩絳,重新戴上,并親切地詢問寶玉的年齡和學(xué)業(yè)。寶玉一一作答。
盡管兩人年齡相差不大,北靜王因身份尊貴,如長輩般關(guān)心寶玉。他見寶玉言辭清晰、談吐得體,便向賈政贊道:“令郎真乃龍駒鳳雛,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將來‘雛鳳清于老鳳聲’,前途無量。”北靜王以“小王”自稱,稱賈政為“世翁”,表示對賈家的尊敬。他用“唐突”一詞,是謙辭,意指自己這樣贊美寶玉是否過于冒昧。但實(shí)際上,這樣的贊美讓賈政十分高興,因?yàn)檫@意味著寶玉的成就有望超越父親。
“雛鳳清于老鳳聲”一句,源自李商隱贊美幕府主人孩子的詩句,后來常用來形容家族中年輕一代的成就將超過老一輩。北靜王以此贊美寶玉,無疑是對他極高的期許。
賈政忙賠笑道:“犬子豈敢謬承金獎(jiǎng)。賴藩郡余禎,若真如您所言,亦是吾輩之幸。”他謙稱寶玉為“犬子”,表示不敢接受北靜王如此高的贊譽(yù)。同時(shí),他也表達(dá)了對北靜王福澤的感激,認(rèn)為如果寶玉真能如北靜王所說,那將是他們家族的幸運(yùn)。
北靜王則進(jìn)一步叮嚀:“令郎資質(zhì)出眾,想必深受老太夫人、夫人鐘愛。但吾輩后生,不宜過于鐘溺。昔我亦曾蹈此轍,想令郎亦未必能免。”他提醒賈政,雖然寶玉聰明可愛,但過分的寵愛可能會(huì)荒廢學(xué)業(yè),他自己就曾犯過這樣的錯(cuò)誤。
接著,北靜王向賈政發(fā)出邀請:“若令郎在家難以用功,不妨常到寒第。吾雖不才,但府中常有海上名士聚會(huì),令郎常來談會(huì),學(xué)問必可日進(jìn)。”他表示,如果寶玉在家難以專心學(xué)習(xí),可以到他的府中來。因?yàn)樗母∈菚r(shí)下精英們常常聚會(huì)的地方,寶玉如果能常來,一定會(huì)有所收獲。
最后,北靜王用了一個(gè)典故“垂青目”來表達(dá)他對寶玉的看重。這個(gè)典故源自魏晉時(shí)期的竹林七賢之一阮籍,他以青眼表示對喜歡的人的看重。北靜王表示,他愿意給寶玉這樣的機(jī)會(huì),讓他在自己的府邸中與名士們交流學(xué)習(xí),希望寶玉能夠因此有所精進(jìn)。
賈政忙鞠躬答應(yīng),顯得對北靜王的話十分恭敬。與寶玉的輕松親切相比,北靜王與賈政的對話更顯正式,帶有幾分八股的味道,他叮囑賈政要好好教育寶玉,切莫荒廢學(xué)業(yè)。
隨后,北靜王將腕上的一串念珠卸下,遞給寶玉,說:“今日初會(huì),倉促之間無敬賀之物,此即前日圣上親賜的鹡鸰香念珠一串,權(quán)作賀禮。”這串念珠是皇帝親賜的,北靜王將其贈(zèng)予寶玉,寓意兩人情誼深厚,如同兄弟。寶玉連忙接過念珠,回身奉與賈政,這是禮節(jié)所在,郡王賜物,需先交由父親。賈政與寶玉一齊向北靜王致謝,場面莊重而溫馨。
關(guān)于這串念珠的香氣“鹡鸰”,雖未有實(shí)物考證,但其在古代文化中象征著兄弟間的友愛之情。《詩經(jīng)》中亦有“鹡鸰”二字,用以表達(dá)深厚的兄弟情誼。北靜王以此念珠贈(zèng)予寶玉,無疑是在表達(dá)他已把寶玉當(dāng)做自己的小兄弟。
送殯隊(duì)伍因王爺駕到而暫停,眾人肅靜回避。賈赦、賈珍等人上前請北靜王先行,卻被婉拒。北靜王表示,逝者已登仙界,非塵世中人可比,自己雖受皇恩,繼承郡王之位,但豈可越靈車而進(jìn)?他言辭謙卑,毫無王爺?shù)闹焊邭獍骸?/span>
賈赦等人見北靜王執(zhí)意不從,只得告辭謝恩,命手下掩樂停音,浩浩蕩蕩的殯葬隊(duì)伍走完,待一切完畢后,北靜王才上轎離開。
北靜王的形象在此段大書特書的描寫,他年輕、聰明、俊美,又如此謙卑,堪稱完美。這種完美正是寶玉所要追求的,身處富貴卻又不失矜持與謙卑。這一段文字美得令人心醉,將寶玉的人生向往通過北靜王的形象,完美地詮釋了出來。
生命無論貴賤,皆值珍視
出殯隊(duì)伍行至鄉(xiāng)下,場景轉(zhuǎn)換,文學(xué)上的鋪排與對比愈發(fā)精彩。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凡,至城門前,賈赦、賈政、賈珍等諸同僚屬下設(shè)祭棚接祭,一一謝過后,方出城直奔鐵檻寺。
鐵檻寺,賈家鄉(xiāng)下家廟,寧、榮二公所設(shè),為家族逝者停靈之地。“鐵檻”即鐵門檻,古代家族地位越高,門檻越高,唐宋文學(xué)中以“門檻”為喻,意指人怕死,故設(shè)高鐵門檻以擋死亡。然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面對死亡。此回中鐵檻寺與饅頭庵之名,皆源于范成大詩句,暗示秦可卿之死。
然而,在這熱鬧場面中,我們幾乎忘卻這是秦可卿的喪事,風(fēng)光與排場更像是一場作秀。賈珍帶賈蓉請長輩上轎上馬,準(zhǔn)備出城。賈赦一輩坐轎,賈珍一輩騎馬。鳳姐因記掛寶玉,怕他縱性逞強(qiáng),不服管教,便命他同坐一車。寶玉只得下車,爬入鳳姐車上,二人說笑前來。寶玉因賈母疼愛、鳳姐擔(dān)心,得以與她同車,享受這份特殊的照顧。
不一時(shí),兩騎快馬飛奔而來,至鳳姐車前,一躍而下,稟報(bào)前方有歇息之處,請鳳姐更衣小憩。原來,郊外房舍稀少,需探路回報(bào)。更衣,實(shí)乃如廁之雅稱。路途遙遠(yuǎn),需尋農(nóng)家小憩,兼作他用。鳳姐聞?dòng)崳凑埿稀⑼醵蛉耸鞠隆5昧詈螅P姐命眾人歇息片刻。于是,轅馬岔出人群,向北疾馳而去,暫離出殯隊(duì)伍。
寶玉車內(nèi),急命人請秦鐘。此時(shí),他心系秦鐘,時(shí)刻掛念。秦鐘正隨父轎而行,忽見寶玉小廝來請,知為打尖之事。“打尖”與“更衣”,皆為休憩之意。如今我們常用“解手”一詞,源于古代移民墾荒之時(shí),人手被綁,唯上廁所時(shí)方得解開,故有此俗稱。
秦鐘見鳳姐車馬北去,后曳寶玉之馬,鞍籠俱全,便知二人同車。于是,自亦帶馬趕上,共入一莊門。賈家聲勢之大,可見一斑。僅因女眷欲更衣,莊中男子皆被驅(qū)離,婆娘亦無處回避,只得任由其便。
村姑莊婦初見鳳姐、寶玉、秦鐘之風(fēng)采,衣飾華美,舉止優(yōu)雅,無不矚目。此情此景,猶如觀戲,令人嘆為觀止。作者于描述北靜王之后,再繪此景,意在對比貴族與農(nóng)家之異同。貴族忽至農(nóng)家,村民之反應(yīng),盡顯人間百態(tài)。
作者回憶一生繁華,卻以平等視角述之,使讀者悟出:每個(gè)生命皆有其獨(dú)特立足角度,無論貴賤,皆值珍視。
寶玉踏入茅堂,便吩咐眾人先去游玩。他隨秦鐘步出,帶著小廝穿梭于莊院間,所見農(nóng)具如鍬、镢、鋤、犁,皆覺新奇,不知其名用途。此景恰映證了“鄉(xiāng)下人”與“貴族”間身份轉(zhuǎn)換的趣味對比,正如書中以出殯一事,巧妙串聯(lián)起北靜王的華貴與二丫頭的質(zhì)樸,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命風(fēng)貌。
寶玉在小廝的解說下,方知每件農(nóng)具背后的辛勞,不禁點(diǎn)頭感嘆:“難怪古詩云:‘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此言非虛。”此番體悟,讓他深切感受到人間煙火的不易,這份深情不僅限于對人,亦及于萬物。寶玉雖時(shí)有叛逆,厭學(xué)貪玩,但若得以適當(dāng)引導(dǎo),非限于死記硬背,而是親歷鄉(xiāng)村、自然,其心境必有不同。
實(shí)際上,寶玉并非真的厭學(xué),當(dāng)他真正理解這些農(nóng)具之時(shí),李紳的詩句自然而然地浮現(xiàn)心頭。這正是寶玉的可貴之處,他內(nèi)心充滿悲憫,悟性極高,從不以貴族身份自居,待人接物皆顯真誠。如此寶玉,實(shí)乃可塑之才。
行至另一房前,寶玉見炕上置有紡車,好奇詢問。小廝告知后,他竟上前擰轉(zhuǎn)玩耍,自得其樂。這一幕,對寶玉而言,紡車不過是新奇玩具,卻惹惱了其主——一位約莫十七八歲的村姑,她擔(dān)憂一日辛勞所紡之線因此凌亂,急忙跑來制止,眾小廝亦連忙阻攔。
面對村姑的“冒犯”,寶玉的反應(yīng)尤為可貴。他非但未怒,反而迅速放手,賠笑道歉:“因未見此物,故而試之。”寶玉之賠笑,盡顯其可愛之處。他常懷歉疚之心,從無權(quán)勢之傲,即便面對鄉(xiāng)間女子,亦無半點(diǎn)盛氣凌人。此等謙遜與體貼,在那個(gè)與民間鴻溝深重的年代,顯得尤為難能可貴。連他身邊的小廝或許都會(huì)仗勢欺人,而寶玉卻以一顆平和之心對人。
“站開了,我紡與你瞧。”二丫頭此言,質(zhì)樸中帶著自信,盡顯鄉(xiāng)間女子的直率與大氣。她雖僅為一介農(nóng)家女,卻樸素大方,健康自然,無絲毫矯揉造作。二丫頭在書中僅一閃而過,卻似在寶玉心中留下了永恒印記。她所代表的生命狀態(tài),是寶玉生平難得的體驗(yàn),那份大大咧咧、黑里透紅的生命力,是他身為貴族子弟永遠(yuǎn)無法觸及的。
人們常道貧窮為憾,卻鮮有人言富貴亦有其憾。曹雪芹之偉大,在于他以平等之筆觸,描繪了不同生命狀態(tài)下的種種遺憾。寶玉這一日,心中滿是對二丫頭生活狀態(tài)的向往,他渴望成為她身邊的一員,體驗(yàn)?zāi)欠菁冋娴纳睢o論寶玉如何度日,其內(nèi)心深處總有一份悵然,因他深知,單一的生命狀態(tài)總是單薄且不足的。
秦鐘的反應(yīng)與寶玉大相徑庭,顯得頗為小家子氣,令人不悅。他初登場便扭扭捏捏,畏懼萬物,雖得寶玉疼愛,本有機(jī)會(huì)接受良好教育,攀升尊貴地位,卻終未能如愿。姐姐出殯之際,他竟在廟中調(diào)戲小尼姑,如今遇見二丫頭,又輕薄言道:“此卿大有意趣。”寶玉待人以尊重,秦鐘卻流露出人性的卑微。
寶玉推開秦鐘,笑斥道:“該死的!再胡說,我就打了。”言罷,轉(zhuǎn)而注視那丫頭紡起線來,此景于他而言,或許新奇非常,他或許從未見過女子紡紗。
正當(dāng)寶玉欲言語時(shí),忽聽那邊老婆子呼喚二丫頭,聲音中帶著驚慌。或許是她母親或祖母,擔(dān)憂二丫頭拋頭露面會(huì)招惹富家公子,得罪不起,更怕被貴族看上,從而陷入悲劇。古時(shí)平民深知,被貴族青睞,往往意味著一生悲劇的開始,寧愿安于農(nóng)家,嫁作農(nóng)民婦。因此,那一聲呼喚,實(shí)則意味深長。二丫頭聞言,即刻丟下紡車,匆匆離去。
二丫頭雖僅在此段露面,卻令人難忘。她的存在,為寶玉的生命添上了獨(dú)特的一筆,與北靜王形成鮮明對比。寶玉深感世間可愛之人甚多,愛之不盡,無論是對北靜王的仰慕,還是對二丫頭的心疼,皆是他深情的體現(xiàn)。寶玉之情,實(shí)則不易懂,然絕非濫情。
“寶玉悵然無趣。”他遺憾未能與二丫頭多言。二丫頭之高,非出身之貴,而是其生命自有之高貴。她雖農(nóng)家出身,地位卑微,但在寶玉眼中,卻高不可攀,因他無法親近。
鳳姐兒遣人來喚,寶玉與秦鐘只得入內(nèi)。鳳姐洗手更衣,問及是否更換衣物,寶玉則否。鳳姐注重路途體面,至鐵檻寺亦講究禮儀。
仆婦們端來行路所需之茶壺、茶杯及十錦屜盒等小食。十錦屜盒,乃錦盒裝盛之各式點(diǎn)心與食物。官家出行,仆人眾多,換洗衣物、飲食皆需備齊,場面之盛大,可見一斑。
“旺兒預(yù)備賞封,賞了本村主人,莊婦等來叩賞。”寶玉留心尋覓,卻未見二丫頭蹤影。顯然,他在尋她,覺剎那緣分已逝,心生悵然與遺憾。唯寶玉對人深情如此,秦鐘則不然,轉(zhuǎn)瞬即忘。寶玉卻覺與二丫頭似有一生一世之緣,無論緣深緣淺,皆需慎重以待。
車行不遠(yuǎn),忽見二丫頭懷抱小弟,與女伴說笑而來。此景雖美,寶玉卻無從再言,因坐鳳姐旁,身份所限,不能隨意搭話,只能擦肩而過。作者此筆,盡顯生命歸屬之異,遺憾反成寶玉之常態(tài)。
“寶玉恨不得下車相隨,然眾人不允,只得目送。”他深感生命中總有未竟之事,此別亦無聲,轉(zhuǎn)眼無蹤。此段描繪寶玉與二丫頭短暫相遇,亦寫盡人間奇特緣分。人生每日,皆可遇此類匆匆相逢與告別。古今中外,鮮有文學(xué)家能描繪此狀,作者卻以大悲憫之筆,寫盡寶玉與二丫頭生命中不能完成之部分,遺憾與珍重并存。或許,寶玉亦在此“了”卻一物。“了”字玄妙,先有舍棄之“了”,方有了悟之“了”。

王熙鳳攬財(cái)包訴訟
“行不多時(shí),又遇大殯。”因靈車行進(jìn)緩慢,故岔路之后迅速重歸其列。尋常作家述出殯即止,然曹雪芹則穿插小插曲,后再回歸主線。
“前方法鼓金鐃,幢幡寶蓋,鐵檻寺接靈眾僧已至。片刻后,入寺另演佛事,重設(shè)香壇。”因需寄靈于此,故舉行儀式,重設(shè)香壇。“秦可卿之義女寶珠,安靈于內(nèi)殿偏室,并伴其側(cè)。”
“賈珍于外款待親友,有擾飯者,亦有辭別而去者。”親友或于賈府即別,或送至鐵檻寺后離去,亦有留下共餐者。“公侯伯子男等依次散去,至未末時(shí)分方盡。”送殯者身份顯赫,輩分高者先行。
“內(nèi)眷則由鳳姐張羅接待,顯官誥命亦依次散去,至晌午大錯(cuò)時(shí)方盡。”“堂客”即內(nèi)眷,自高官夫人始,歷時(shí)良久方散。“唯數(shù)近親,待三日安靈道場后方離去。”寶玉與秦鐘亦留宿。
“邢、王二夫人知鳳姐不能歸家,亦欲進(jìn)城。王夫人欲帶寶玉同往,然寶玉初至郊外,不肯歸,愿與鳳姐同住。”眾孩童平素家中管束甚嚴(yán),鮮有機(jī)會(huì)外出,此次出殯對他們而言猶如郊游,欲借此機(jī)嬉戲。“王夫人無奈,只得將寶玉交與鳳姐,遂歸。”
鐵檻寺,原為寧、榮二公所建。古時(shí)大戶人家,常購地建廟,將周邊土地租予農(nóng)民,以租金供廟中香火,以備族中之人“老去”。京城有人逝世,遺體便寄放于此,鐵檻寺因而成為賈府的私家殯儀館。
“寺內(nèi)陰陽兩宅,均已預(yù)備妥當(dāng),可供送靈之人寄居。”“陰宅”為寄靈之所,“陽宅”則為送靈之人居所。然賈家“后輩人口繁盛”,已至三百余人,“貧富不一,性情各異”。“參商”乃天上永不相見之星辰,喻家族中人之差異。有安分守己、家道中落者住于此;而有錢勢排場之人,則嫌此處不便,另尋村莊或尼庵為宴退之所。
“族中諸人皆于鐵檻寺下榻,唯鳳姐嫌其不便,遂早遣人至饅頭庵,與姑子凈虛商議,騰出兩間房作為居所。”鳳姐覺尼姑庵更為潔凈便利,故不住鐵檻寺,而選擇饅頭庵。寶玉與秦鐘亦隨其前往饅頭庵。
作者巧思,對比“鐵檻”與“饅頭”之名,卻不愿作品過于寓言化或哲學(xué)化,故筆鋒一轉(zhuǎn),言饅頭庵原名水月庵,因饅頭美味,眾人戲稱之為饅頭庵。若直言因人死后歸墳冢,則顯俗氣。此等文學(xué)真假,實(shí)為《紅樓夢》之趣,作者屢言:假做真時(shí)真亦假,喜玩真假游戲,令人感生命之荒謬,常以假為真。
鳳姐遂于饅頭庵下榻,與主持凈虛言談。凈虛述一趣事:城中有巨富張家,女金哥,自幼許配守備之子。后張家又識(shí)李衙內(nèi)家,家世更顯赫,張家欲嫁女于李家。兩家因此紛爭,訴至公堂。一老尼姑竟欲插手此事,求鳳姐向節(jié)度使言,使守備家退婚,金哥便可順利嫁入李家。
此事與秦可卿出殯無直接關(guān)聯(lián),卻揭示了貴族家庭之復(fù)雜關(guān)系,尤其是與和尚廟、尼姑庵之糾葛,遠(yuǎn)非表象之簡單。凈虛之名,實(shí)則既不凈亦不虛。她求助于鳳姐,鳳姐則大膽借賈璉之名發(fā)函,事成后收取三千兩銀子,而賈璉渾然不知。
秦可卿之死,對王熙鳳而言,乃一轉(zhuǎn)折點(diǎn)。自此,她開始協(xié)理寧國府,管家之才得以顯現(xiàn)。然正因如此,她之膽子愈發(fā)壯大,乃至包攬?jiān)V訟。此事于她而言,輕而易舉。賈家聲勢浩大,只需以賈家之名發(fā)函,官員們便不敢不從,銀子隨即送來。此后,此類事情她愈辦愈多。
王熙鳳之步步靠近權(quán)力,并非初衷即玩弄權(quán)勢。實(shí)則家世為其支撐,隨意一發(fā)函,便有三千兩進(jìn)賬。作者巧妙揭示豪門貴族如何不知不覺踏上違法之路。貪贓枉法之心,往往于無形中日漸累積。借秦可卿喪事之機(jī),作者逐步將此等事件展現(xiàn)于讀者眼前。
秦鐘之父秦業(yè),年邁多病,未能久留。于女兒喪事,父親之角色并非核心,遂離去,命秦鐘留守三日,以待安靈。秦鐘遂與鳳姐、寶玉同至水月庵。凈虛座下二徒,智善與智能兒,出迎眾人。
趣事由此起,小尼姑智能兒對秦鐘心生愛慕,二人間關(guān)系微妙。鳳姐目光敏銳,察覺智能兒許久未見,愈發(fā)俊俏:“鳳姐至凈室,更衣凈手后,見智能兒身形愈長,模樣愈發(fā)出眾,便道:‘師徒二人怎許久未至我府?’”
前文提及,凈虛曾攜智能兒至賈府領(lǐng)取月供銀兩,智能兒與惜春嬉戲。惜春當(dāng)時(shí)尚幼,戲言欲效仿智能兒,剃發(fā)為尼。時(shí)光荏苒,《紅樓夢》中人物皆處成長之年,智能兒亦悄然蛻變。鳳姐憶起昔日孩童模樣的智能兒,如今已初具少女風(fēng)姿,言語間流露出對往昔時(shí)光的懷念。

少年男女的情欲糾葛
不言老尼陪伴鳳姐,且看秦鐘、寶玉二人于殿上嬉戲。此段筆觸奇特,雖寫喪事,卻蘊(yùn)含人性觀照,即便出殯之時(shí),亦與平常無異。
寶玉聰慧,早察秦鐘與智能兒眉來眼去,私下或已情深。遂故意逗之,笑道:“能兒來了。”秦鐘則回應(yīng):“理她作甚?”秦鐘性格微妙,一向卑微,后因?qū)氂癖幼o(hù)疼愛,漸顯傲慢。他私下與智能兒調(diào)情,然寶玉提及,卻故作輕視。
孩童之心,往往如此,對一人特好,卻于眾人前表示疏離。可見秦鐘乃平凡少年,與寶玉迥異。寶玉尊重眾人,秦鐘則情緒多變,時(shí)而怯弱,時(shí)而囂張。打架時(shí),稍有擦傷便哭鬧撒嬌,因知寶玉疼愛。
寶玉與秦鐘相處短暫,至第十六回,秦鐘即逝。我常思,秦鐘之命,可用二字概括——福薄。寶玉、賈母、鳳姐皆疼愛他,然他承受不起此福。下文已伏秦鐘悲劇之線,他怯弱、體弱,有女兒般柔弱之象。
寶玉笑而諷之:“那日于老太太屋中,無人之際,你摟他何為?今又欺我。”寶玉心如明鏡,早已洞察一切。他與秦鐘間,頗有戀愛之感,疼愛秦鐘至極。然秦鐘另有所愛,寶玉亦覺理所當(dāng)然。寶玉之性,寬廣而深邃,此乃對人性之天生理解,亦即我們所言之深情。他不計(jì)較小事,胸懷大度。
秦鐘笑而否認(rèn):“此言差矣。”其不敢面對所為,寶玉則笑言:“承認(rèn)與否,我不在乎。你只叫他來,為我倒碗茶便罷。”秦鐘又笑:“此又何奇?你命他倒,他豈敢不從?何須我言?”此段對話,雖顯無聊,然其中意趣盎然。
寶玉地位顯赫,為富家公子,眾人皆寵。他若命智能兒倒茶,智能兒必從。然他特命秦鐘呼之,蓋因覺秦鐘與智能兒間有特別之情。此時(shí)可見,寶玉從無霸占秦鐘之心,反覺秦鐘與智能兒相配甚好,借此機(jī)促其更進(jìn)一步。寶玉言道:“我命她倒,無情意;你命她倒,則含情意。”此言出自少年之口,頗顯特別。無聊言談間,寶玉性格之奇特一面顯露無遺。世俗之嫉妒、吃醋、霸占之心,寶玉皆無。他覺有情便是好,秦鐘愛智能兒,他亦覺佳。秦鐘無奈,終言道:“能兒,為我倒碗茶來。”
智能兒自幼在榮府穿梭,無人不曉,常與寶玉、秦鐘嬉笑。及至年長,漸悟風(fēng)月,遂對秦鐘之風(fēng)流人物心生愛慕,而秦鐘亦極愛其妍媚之姿。“妍媚”二字用于尼姑,頗顯意趣。少女雖剃發(fā),然肌膚眉眼間,少女之感仍躍然紙上。此二字不僅寓其貌美,更含女性之嫵媚。
二人雖未越軌,然情已相投。今智能見秦鐘,心花怒放,即去倒茶而來。“心眼俱開”,此詞妙極。他們月僅一見,且隨年齡增長,接觸愈難。因喪事之機(jī),智能得見心儀之人,欣喜不已。寶玉洞察一切,便有意促成此事。在他看來,人間有情,便是美好。
寶玉內(nèi)心亦矛盾,常感無所適從。北靜王、秦鐘、二丫頭、黛玉,皆情深意重,然皆含遺憾,終有些許無奈。他欣賞他人之情,卻置身事外,享有一份幸福感。茶至,秦鐘笑言:“給我。”寶玉亦笑言:“給我!”猶如兩童爭搶,實(shí)則寶玉戲耍而已。他自信滿滿,于寵愛中成長,最大愿望乃將所得之愛,與眾人共享。此乃逗秦鐘之舉也。
智能兒抿嘴笑道:“一碗茶也爭,我手中莫非有蜜?”此言難以捉摸,輕佻則失當(dāng),恰到好處則盡顯童真爭奪之趣,分寸頗難拿捏。寶玉先奪得茶,品飲間欲發(fā)問,卻見智善來喚智能擺設(shè)茶碟。片刻后,智善邀二人共品茶果點(diǎn)心。智善性情憨厚,或許少了些妍媚之氣,故無人撩撥。她喚智能備茶,欲款待寶玉、秦鐘。“然二人對此并不在意,僅稍坐片刻,便又外出嬉戲。”富家公子,慣于精致美食,對廟中粗茶淡飯,自不以為意。
場景一轉(zhuǎn),另起一幕,鳳姐于大堂與凈虛言談之景躍然紙上。

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里
實(shí)際上,這張姓財(cái)主本已將女兒許配給守備之子,然如今又遭有權(quán)有勢的李衙內(nèi)青睞。凈虛雖稱張家為舊時(shí)施主,實(shí)則或亦暗中圖利。她言道:“張家欲退守備之親,又恐其不允,故謊稱女兒已有所歸。豈料李公子執(zhí)意不從。”
張家財(cái)主左右為難,女兒嫁于哪家皆可,然兩家皆為官宦,均不讓步。守備家聞此,不問青紅皂白,便前來辱罵,言其一女許多家,且拒退定禮,竟打起官司。張家焦急,只得派人上京尋求解決之道,決心要退定禮。
凈虛為張家指點(diǎn)迷津,言道長安節(jié)度使云光老爺,乃此地最大之官,若其出面,守備必退婚。而云光與賈府交好,故欲求賈家相助。世人皆以為出家人不應(yīng)涉此俗事,然凈虛竟對此中關(guān)系了如指掌,知求何人方有效。
凈虛懇求賈府相助,言道:“望太太與老爺修書一封,求云老爺與守備說和。守備乃節(jié)度使下屬,長官出面,其不得不從。”并暗示張家愿出重金以報(bào)。此言一出,賈府是否能助張家解此困境,便成了眾人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
鳳姐聞言笑道:“此事雖小,卻非太太所管。”此言一出,盡顯鳳姐之機(jī)智,先以王夫人不涉此事為由擋之。老尼隨即應(yīng)變:“太太不涉,奶奶便可做主。”老尼姑步步為營,先抬出王夫人,見鳳姐阻攔,便直接轉(zhuǎn)向于她。
鳳姐再笑:“我非缺銀之人,亦不為此等事。”言下之意,我非為錢,若要管,必有所圖,一語雙關(guān),機(jī)智盡顯。老尼姑聽后,似自言自語般嘆道:“雖如此,張家已知我來求府,若不管,似府里無能一般。”此語實(shí)為激將,深知權(quán)勢之家最怕被人言無能。
果然,鳳姐被激,言必管此事。此情此景,盡顯人情世故之復(fù)雜。寶玉、秦鐘、智能兒那邊天真爛漫,情欲萌動(dòng);而這邊凈虛與王熙鳳卻是在玩弄權(quán)謀,老謀深算。作者借秦可卿之喪禮,展現(xiàn)人性之多樣,而這一切恰在饅頭庵中發(fā)生。
若“饅頭庵”真為“土饅頭”之暗示,則此情節(jié)更顯諷刺之意。唐代王梵志詩云:“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里。”意指城外土饅頭之餡,皆來自城中之人。此為禪宗之狠辣偈語,警示世人,死亡與每個(gè)人息息相關(guān)。而今觀饅頭庵中,清凈之地卻發(fā)生情欲與訴訟之事,人之難以覺悟,可見一斑。
鳳姐聞此言,興頭頓起,笑道:“你素日知我,我從不信陰司地獄報(bào)應(yīng)。凡事我說行便行。叫他拿三千銀子來,我替他出氣。”此言一出,鳳姐之潑辣盡顯,被激之下,她定要表現(xiàn)一番。常人不敢如此直言,而鳳姐之厲害,恰在于此。她直言不信報(bào)應(yīng),決定插手此事。
老尼聞之,喜形于色,忙道:“有,有!此事不難。”見王熙鳳已明言要三千兩銀子,她心知事成。
鳳姐再言:“我非他們扯篷拉牽之徒,圖此銀子。這三千兩,不過是給小廝作盤纏,賺些辛苦錢。我分文不取,便是三萬兩,我此刻也能拿出。”言下之意,她并不在乎此銀,只是為小廝考慮。然實(shí)際上,她怎會(huì)輕易給小廝三千兩?能給二十兩已是極限。
事實(shí)上,那三千兩銀子最終落入了王熙鳳之手。一次,賈璉在場時(shí),王熙鳳詢問來訪者,平兒機(jī)智應(yīng)對,假稱香菱來訪,一番周旋后支走了賈璉。隨后,王熙鳳問起真相,平兒笑道,哪有什么香菱,是旺兒媳婦送來了三千兩的利銀。原來,鳳姐已將這筆銀子放了高利貸,如今利息到賬,她的膽子也愈發(fā)大了起來,不僅插手訴訟,還涉足高利貸,貪婪本性逐漸顯露。
老尼見狀,連忙應(yīng)承,并催促道:“既如此,奶奶明日便開恩處理了吧。”王熙鳳得意洋洋,她在兩府間不可或缺,即便喪事期間,他人已散去,她仍堅(jiān)守崗位,彰顯其重要性。老尼恭維道:“這點(diǎn)小事,在他人那里或許手忙腳亂,但在奶奶面前,再多也不費(fèi)吹灰之力。
正所謂‘能者多勞’,太太因奶奶處事妥當(dāng),凡事都交由奶奶,奶奶也需保重身體啊。”老尼姑的言辭中充滿了贊美,她的成功并非偶然,廟宇香火鼎盛,得益于她圓滑的處世之道,她擅長籌款,更善于籠絡(luò)人心,言辭之中滿是恭維與奉承。
“一路奉承,鳳姐越發(fā)受用,忘卻勞乏,攀談不止。”人人愛聽好話,鳳姐尤甚,她渴望被捧,渴望展現(xiàn)能力。然而,這恰恰成了她的軟肋,被老尼姑巧妙利用。人難時(shí)刻保持清醒,鳳姐雖聰明,此刻卻未察覺陷阱,已深陷其中。
作者筆鋒一轉(zhuǎn),如電影剪接,畫面切至秦鐘與智能兒。十五回后半,雙線并行:一線是凈虛與鳳姐,一線是智能兒、秦鐘與寶玉。為何交替?多讀《紅樓夢》,我們不禁要問:為何將這兩段看似無關(guān)的內(nèi)容并置?一者司法案件,一者情欲糾葛,何以同述?
實(shí)則,作者意在探討同一主題——人之不自覺的欲望。秦鐘、鳳姐之欲,皆在此刻萌芽。他們不知人為何物,連修行中的凈虛亦懵懂無知,終鑄大錯(cuò)。于土饅頭中談?wù)加小⒂冂娕R終仍沉溺其中,可見《紅樓夢》之警醒無處不在。

睡下再細(xì)細(xì)算賬
在那個(gè)時(shí)刻,秦可卿與喪事的記憶仿佛被集體抹去,喪事竟成了一場異樣的狂歡,夜幕降臨時(shí),廟內(nèi)已有人開始放縱。而秦鐘,趁著夜色掩護(hù),悄悄尋覓智能兒。他抵達(dá)后房,只見智能孤身一人,正忙著洗茶碗,小尼姑的生活尤為艱辛,尤其是那些出身貧寒、被迫賣身入寺者,終日勞作不息。智能兒或許也渴望逃離這無盡的勞役,她日復(fù)一日,從早忙到晚,連與秦鐘簡短交談也被智善打斷,喚去執(zhí)行任務(wù)。
秦鐘的到來,打破了這份沉寂,他毫不猶豫地?fù)ё≈悄埽H昵之舉躍然紙上。這樣的描寫,在當(dāng)時(shí)顯得尤為大膽,甚至可能被視為對佛門的不敬。畢竟,尼姑庵內(nèi)怎可發(fā)生如此之事?然而,作者早已洞察人性深處,毫不避諱地展現(xiàn)其真實(shí)面貌。事實(shí)上,歷史長河中不乏此類事例:唐玄宗對壽王妃的癡戀,乃至其出家后仍難舍舊情,終使楊貴妃之名響徹史冊;武則天亦曾在唐太宗駕崩后遁入空門,卻與高宗暗生情愫,重歸宮廷,成為一代女皇。
作者深知,于上流社會(huì)而言,佛法往往不過是一場形式,清修之實(shí)早已名存實(shí)亡。這些揭示,即便今日讀來,仍令人震撼不已,引人深思。在那個(gè)光鮮亮麗的世界里,人性的復(fù)雜與社會(huì)的真實(shí)面貌,遠(yuǎn)比表象更為豐富多彩,引人探究。
在作者的筆下,智能兒并非僅僅是一位出家人,而是一個(gè)鮮活的少女,剃發(fā)修行僅是命運(yùn)使然,家境貧寒迫使她踏上這條道路。她無辜而純真,同樣擁有追求愛情的權(quán)利。從保守視角審視,《紅樓夢》無疑逾越了諸多禁忌;然而,現(xiàn)代眼光下,我們卻能察覺到作者在那個(gè)時(shí)代便已大膽挑戰(zhàn)傳統(tǒng)觀念,仿佛在質(zhì)問:為何尼姑便不能擁有愛情?從現(xiàn)代主義角度解讀,《紅樓夢》充滿了活潑與前衛(wèi)的元素。
智能兒的反應(yīng)復(fù)雜而微妙,她身為佛門中的清修尼姑,面對秦鐘的親近,內(nèi)心掙扎不已。“這算什么!再這樣,我就叫喚。”她的反應(yīng)是對道德的堅(jiān)守,試圖抗拒這份不合時(shí)宜的情感。然而,她并未堅(jiān)決拒絕,因?yàn)樾闹型瑯訉η冂姳в袗垡狻W髡呒?xì)膩地刻畫了這種矛盾心理:不喜歡時(shí)的抗拒與喜歡時(shí)的抗拒截然不同。智能兒雖跺腳責(zé)罵,卻未真正呼喊,因?yàn)樗钪坏┖艉埃磺袑o法挽回。
秦鐘急切地懇求:“好人,我已急死了。”這里的“急死了”是對少年情欲的直接描繪,與賈瑞身上的沖動(dòng)如出一轍。他甚至以死相逼:“你今兒再不依,我就死在這里。”可見,這并非秦鐘的首次請求,智能兒之前已多次拒絕。智能兒回應(yīng)道:“你想怎樣?除非等我出了這牢坑,離了這些人,才依你。”她將尼姑庵視為牢坑,字里行間透露出她并非自愿修行,而是身陷囹圄,渴望逃離。
提及一出戲,名為《思凡》,某些出家人非常反對。此劇講述一位尼姑在廟中,一面拜菩薩,一面拜羅漢,卻內(nèi)心獨(dú)白,傾訴自己可憐的情欲,最終決定下山逃離。這出戲情感深沉,觸動(dòng)人心。我們深知,并非所有出家人都如此,真正基于信仰的修行者,自不會(huì)陷入此般困境。《思凡》中的尼姑,實(shí)則是被迫出家,觀眾對她充滿同情,這與《紅樓夢》中智能兒的遭遇頗為相似。
在這場戲中,秦鐘的欲望與智能兒的悲苦交織在一起。若以悲憫之心觀之,這不僅僅是一場調(diào)情戲,更透露出智能兒的痛苦與無奈。秦鐘并非可靠之人,即便此刻得手,轉(zhuǎn)眼便可能忘懷。智能兒似乎也有所察覺,她深知自己吸引秦鐘,僅因他尚未得手,因此她不肯輕易屈從。
秦鐘言道:“這也容易,只是遠(yuǎn)水救不得近渴。”他的言語直率,透露出少年的沖動(dòng)與欲望。“近渴”即是他難以克制的情欲。接著,他吹熄燈火,滿屋漆黑,將智能兒抱至炕上,二人便纏綿起來。這是作者極為大膽的描寫,既漠視了修行之道,又顛覆了傳統(tǒng)禮教。讀來不禁讓人感到一絲悲憫與無奈,因?yàn)樵谀菚r(shí),人往往難以自控。
最有趣的一幕發(fā)生了,秦鐘真欲火焚身,做的起勁時(shí),寶玉竟在此刻闖入。“正當(dāng)二人沉浸其中,忽有一人悄無聲息地進(jìn)來,按住他們,二人驚愕萬分,不敢動(dòng)彈。”尼姑庵中發(fā)生此等事,無疑是驚天大事,兩人皆嚇得魂飛魄散。“只聽那人‘嗤’的一聲笑出,二人聞聲,方知是寶玉。”寶玉總愛搞些惡作劇。
他與秦鐘同住,發(fā)現(xiàn)秦鐘不在,便去尋找,不料撞見了這一幕。寶玉心地善良,他雖調(diào)皮,卻也在暗中提醒他們,以免被他人發(fā)現(xiàn),那后果將不堪設(shè)想。他嚇唬他們,但又不失分寸,用了一種頑皮的方式按住他們。
秦鐘卻是個(gè)呆子,未能領(lǐng)會(huì)寶玉此刻出現(xiàn)的深意,連忙起身抱怨:“這算什么?”寶玉笑道:“你倒不滿,那咱們就叫喊起來。”言下之意,你別傻了,此時(shí)還抱怨我,若真叫起來,引人前來,看你如何收場?
智能兒羞愧難當(dāng),趁夜色匆匆逃離。寶玉拉著秦鐘走出,戲謔道:“你還敢與我爭辯嗎?”前文曾提及,寶玉曾質(zhì)問秦鐘,在老太太房中無人之時(shí),為何摟著智能兒,秦鐘卻矢口否認(rèn)。此刻,秦鐘無奈笑道:“好人!只求你別讓眾人知曉,你要怎樣,我都依從。”他竟向?qū)氂袢銎鹆藡伞氂裥Υ穑骸按丝滩槐囟嘌裕龝?huì)兒睡下,咱們再細(xì)細(xì)算賬。”
此段描寫微妙至極,展現(xiàn)了寶玉與秦鐘之間微妙的情感糾葛。作者以調(diào)皮之筆,勾勒出少男少女間性的混亂與懵懂。對于具體發(fā)生了何事,作者并未明言,僅留下一句“睡下再細(xì)細(xì)算賬”,引人遐想,回味無窮。

寬衣安歇之時(shí),鳳姐在內(nèi)室,秦鐘、寶玉則在外間,地下滿是仆婦,打鋪?zhàn)G冂娤惹爸e,實(shí)屬大膽,情欲之下,全然不顧大體。鳳姐或許會(huì)問起秦鐘去向,寶玉將其找回,亦有幾分顧及顏面之意。“鳳姐因怕通靈玉遺失,待寶玉睡下,便命人取來置于自己枕邊。”鳳姐之細(xì)心,可見一斑,瑣事亦考慮周全。
“寶玉與秦鐘究竟算了何賬?我未曾親眼目睹,不敢妄言。”作者此筆,實(shí)為調(diào)皮,引人遐想。他明知少男少女間會(huì)有何種把戲,卻故作懸念,不言明賬目之事。讀者因此而更加留意那句未明之言。
次日清晨,賈母、王夫人派人來探寶玉,囑其添衣速歸。然寶玉貪玩,不愿離去。秦鐘因戀著智能兒,亦無歸意。鳳姐則另有盤算,多留一日可顯其盡責(zé),同時(shí)亦可借機(jī)辦理凈虛所托之事。三人各有心思。
鳳姐對寶玉道:“我事已畢,你若想逛,我便陪你辛苦一日。但明日必須回去。”寶玉聞言,千求萬求,只愿再留一日。鳳姐無奈,只得應(yīng)允。于是,三人又留宿一夜。
鳳姐遂命貼身管家來旺兒,悄聲告知昨日老尼之事。來旺兒聞后,心領(lǐng)神會(huì),急忙進(jìn)城尋得主文相公,即今日所稱之“代書”,專為人撰寫文書。他假借賈璉之名,修書一封,連夜送往長安縣。
王熙鳳行事大膽,欲取這三千兩銀子,卻不敢用自己的名義,于是假托丈夫賈璉之名寫信。信送至節(jié)度使云光處,云光見信上印有賈璉的印信,又念及與賈府的舊情,便立刻應(yīng)允此事,并回信給來旺兒。此事暫且按下不表。
又過一日,鳳姐等人與老尼姑凈虛告別,囑咐她三日后前往賈府探聽消息。她暗示凈虛,事情已辦妥,但需送錢來方能告知結(jié)果。此間,秦鐘與智能兒戀情纏綿,背地里多次幽會(huì),約定密語,種種情狀,不必細(xì)述,只知二人含情脈脈,依依惜別。

曹雪芹(約1715年5月28日—約1763年2月12日),名霑,字夢阮,號(hào)雪芹,又號(hào)芹溪、芹圃,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的作者,祖籍存在爭議(遼寧遼陽、河北豐潤或遼寧鐵嶺),出生于江寧(今南京),曹雪芹出身清代內(nèi)務(wù)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寧織造曹寅之孫,曹顒之子(一說曹頫之子)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幼子夭亡,他陷于過度的憂傷和悲痛,臥床不起。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除夕(2月12日),因貧病無醫(yī)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