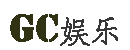冬天漫游:探索劉起與本雅明筆下的詩(shī)意旅程與現(xiàn)代都市生活
劉起
冬天是最適合游蕩的季節(jié)。本雅明在《發(fā)達(dá)資本主義的抒情詩(shī)人》中,有一段關(guān)于大仲馬《巴黎的莫希干人》的描寫(xiě)——書(shū)中主人公決定跟隨他拋在空中的一片紙去尋求冒險(xiǎn)。
這樣漫無(wú)目的的旅程,使沉重的肉身,有可能脫離機(jī)械單調(diào)的日常生活,變得輕盈與詩(shī)意。米蘭·昆德拉所說(shuō)的「人在無(wú)限大的土地之上,一種幸福無(wú)所事事的冒險(xiǎn)旅行」,大致就是這樣一種漫游吧。
本雅明筆下的漫游者是大城市的產(chǎn)物。十九世紀(jì)的現(xiàn)代化大都市巴黎,伴隨現(xiàn)代性的出現(xiàn),人類(lèi)社會(huì)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和情感關(guān)系,發(fā)生了某種顛覆性的改變。馬克思說(shuō)「一切堅(jiān)固的都煙消云散了」,古典時(shí)期穩(wěn)定、堅(jiān)固、完整的生命體驗(yàn),被碎片化了。
這種新的心理機(jī)制和行為方式,帶來(lái)一類(lèi)新的人群——漫游者。漫游者隱身于巴黎街頭千百過(guò)客間,既冷眼旁觀,又不由自主的陷入人潮,形成一種都會(huì)景觀,也預(yù)言都會(huì)現(xiàn)代性的來(lái)臨。漫游者在擁擠不堪的人流中漫步,「張望」決定了他們的整個(gè)思維方式和意識(shí)形態(tài)。
電影是現(xiàn)代性的另一產(chǎn)物。在此之前,沒(méi)有一類(lèi)藝術(shù)形式能像電影一樣展現(xiàn)連貫的時(shí)間與空間,影像最迷人之處正在于此。
然而,由于膠片的物理特性和現(xiàn)實(shí)的種種限制,完整連續(xù)的現(xiàn)實(shí)空間,在影像中被碎片化了。在漫游者的行走中,碎片化的地理空間被串起來(lái),空間的連續(xù)性便得到了救贖。正因如此,電影特別迷戀呈現(xiàn)漫游者的形象。
漫游者的偶遇與愛(ài)情
本雅明筆下的漫游者中最浪漫是波德萊爾《給一位交臂而過(guò)的婦女》的那位多情路人。在喧囂的街頭,主人公對(duì)一位迎面走來(lái)的婦女一見(jiàn)鐘情,這瞬間迸發(fā)的迷戀,卻隨著兩人擦肩而過(guò)轉(zhuǎn)瞬即逝。波德萊爾描述的這種現(xiàn)代性的邂逅方式,因?yàn)槠鋹?ài)情的難以捕捉而更加迷人。
沒(méi)有比新浪潮導(dǎo)演侯麥更擅長(zhǎng)講述這類(lèi)漫游者的偶遇與愛(ài)情了。侯麥影像中的男男女女,似乎總是在走路,行走中的大段的對(duì)白甚至構(gòu)成了影片的主體。鏡頭跟隨人物,走過(guò)街道與巷落,走過(guò)沙灘和花園,從一家咖啡館到另一家。

《午后之愛(ài)》
從六十年代的六個(gè)道德故事系列,到九十年代的四季,所有的邂逅與巧合似乎都發(fā)生在一次次游蕩中。侯麥電影中的整個(gè)城市空間,顯得就像是一個(gè)純粹可能性的景域,從中產(chǎn)生突發(fā)的誤認(rèn)和巧合的邂逅。漫游者們?cè)谝淮未斡问幹信加鰫?ài)情,有心動(dòng)、有曖昧、有失望,也有奇跡。
《面包店的女孩》中,大學(xué)生愛(ài)上了總是每天傍晚與他擦身而過(guò)的女孩,當(dāng)他終于鼓起勇氣搭訕并定下第一次約會(huì)后,女孩卻爽約消失了。為了再次偶遇女孩,他整日游蕩。為了消磨漫長(zhǎng)的游蕩時(shí)間,他走進(jìn)街角的面包店,與面包店的女孩調(diào)情。當(dāng)他終于與面包店女孩有了進(jìn)展時(shí),從前的女神卻忽然再次出現(xiàn)。

《面包店的女孩》
原來(lái)女神并不是爽約,而是在約會(huì)前摔傷了腿,每天在家無(wú)法下樓,卻如此湊巧的在窗前看到了大學(xué)生的三心二意。這個(gè)愛(ài)情故事奠定了侯麥大部分愛(ài)情故事的模式——漫游者的愛(ài)情,充滿(mǎn)了偶遇的不確定性。
夏天是愛(ài)情與偶遇的季節(jié),侯麥的《夏天的故事》中的男孩卡斯巴,在度假別墅等待女友蕾娜,蕾娜遲遲不來(lái),苦了等待的人。正覺(jué)無(wú)趣的卡斯巴遇到了熱烈直率的瑪戈,他們?cè)谏碁┥稀⑿缴稀啾谏稀r石上的一次次散步、聊天,似乎動(dòng)搖了卡斯巴的等待,卻無(wú)法讓卡斯巴接受瑪戈。

《夏天的故事》
卡斯巴與狂野迷人的蘇蓮一見(jiàn)鐘情。似乎為了懲罰他的搖擺不定,蕾娜突然出現(xiàn)。難以抉擇的卡斯巴只能落荒而逃了。這樣的男主角,如果出現(xiàn)在別的故事中,一定很討人厭。但布列塔妮的海岸充滿(mǎn)了愛(ài)情的氣息,我們似乎也無(wú)法責(zé)備卡斯巴的心猿意馬。更何況,侯麥擅長(zhǎng)把曖昧拍得干凈清澈,因?yàn)樗械男膭?dòng)、曖昧都發(fā)生在無(wú)目的的漫游中,所以一切都變得可有可無(wú),也就談不上什么背叛了。
《綠光》則是一場(chǎng)尋找幸福的冒險(xiǎn)旅程。堂吉訶德式的女主角,夢(mèng)想著愛(ài)情,無(wú)法忍受蒼白平淡的現(xiàn)實(shí),因此她在現(xiàn)實(shí)中注入夢(mèng)想,踏上尋找幸福的旅行。然而整個(gè)假期,她都那么孤單,她心神不寧地游蕩在巴黎與鄉(xiāng)間,始終顯得無(wú)所適從。

《綠光》車(chē)站里的邂逅
夢(mèng)想似乎在摧毀著她的現(xiàn)實(shí):旅途中的一切都并不美好,艷遇那么乏味而輕浮,聚會(huì)那么無(wú)趣而膚淺,與陌生人無(wú)法交流,閨蜜也不能理解她。在馬賽海邊,她聽(tīng)到了綠光的傳說(shuō):誰(shuí)能看到綠光,誰(shuí)就能得到幸福。落寞的她在假期結(jié)束返回巴黎的途中,偶遇了一個(gè)男子,兩人一起去海邊看日落。當(dāng)綠光奇跡般的閃現(xiàn)時(shí),她也找到了幸福。
侯麥很狡猾,他似乎告訴觀眾,漫游不過(guò)是一場(chǎng)假想的冒險(xiǎn),可能什么都不會(huì)發(fā)生。但結(jié)尾,他又給了我們一個(gè)小小的奇跡,讓這場(chǎng)漫游變成一次尋找青鳥(niǎo)的幸福旅程。
漫游者的都會(huì)游戲
與侯麥電影中那些只顧著戀愛(ài)的夢(mèng)想家不同,法國(guó)喜劇導(dǎo)演塔蒂電影中的于洛先生,卻是純粹的漫游者。塔蒂通過(guò)影像或可視底片的簡(jiǎn)單組合來(lái)記錄于洛的一次次游蕩。現(xiàn)代都市空間在他的游蕩中,變得清晰起來(lái),一切細(xì)節(jié)都被放大,就如本雅明所說(shuō),大城市并不在那些由它造就的人群中的人身上得到表現(xiàn),相反,卻是在那些穿過(guò)城市,迷失在自己的思緒中的人那里被揭示出來(lái)。
于洛先生是這樣的:穿著寬下擺的風(fēng)衣,瘦腿褲子永遠(yuǎn)短一截,嘴里叼著長(zhǎng)煙斗,走起路來(lái)身體前傾,似乎馬上要跌倒。他溫文爾雅、卻又跌跌撞撞,顯得那么不合時(shí)宜。在城市中游走、在建筑中迷失、在人群中惶惶不安的于洛,總處在一種失神的狀態(tài),他在迷迷糊糊中擾亂了一切,卻對(duì)身邊的混亂渾然不覺(jué)。這種漫不經(jīng)心正是屬于漫游者的特質(zhì)。

《于洛先生的假期》
《于洛先生的假期》描述于洛的一次海濱度假。并沒(méi)有什么戲劇性的事件,只有海灘上的游戲、餐館里的晚餐,娛樂(lè)室里的乒乓球賽,旅館里的假日舞會(huì),從人們來(lái)到海邊,到片尾人群一一離開(kāi),期間什么都沒(méi)有改變,這似乎是一次再平常不過(guò)的假期。
然而,影片從始至終都閃現(xiàn)出一種輕盈的詩(shī)意。于洛一到旅館就引起了一系列的混亂和無(wú)序。無(wú)論是每天的用餐及晚上的娛樂(lè),還是海灘上的休閑活動(dòng)及集體出游,只要于洛在,規(guī)律刻板的生活總會(huì)被他不經(jīng)意地?cái)_亂。

《于洛先生的假期》
出游活動(dòng)中于洛一動(dòng)就壞的老爺車(chē)出了毛病,意外打擾了一場(chǎng)葬禮。冷清的化裝舞會(huì)上只有裝扮成海盜的于洛和一個(gè)姑娘旁若無(wú)人地跳舞。這些混亂但缺少邏輯關(guān)聯(lián)的事件,具備了漫游這一行為的特質(zhì)——零散而無(wú)目的。
《我的舅舅》所呈現(xiàn)的于洛的日常生活,就像是從時(shí)間之流中任意截取的一段,似乎于洛一直就以這樣閑逛的方式生活著。《游戲時(shí)間》由于洛的一次漫游展開(kāi):于洛到巴黎郊外一座現(xiàn)代化的辦公大廈探訪(fǎng)某人,卻在迷宮一般的大樓里迷路了。他進(jìn)入一個(gè)現(xiàn)代商品展銷(xiāo)會(huì),見(jiàn)識(shí)了各種稀奇古怪的產(chǎn)品。晚上,于洛在街上邂逅一個(gè)老朋友,并被邀請(qǐng)參觀了老友的現(xiàn)代化住宅。

《我的舅舅》
出來(lái)后,于洛先生無(wú)意進(jìn)入一家新開(kāi)張的高級(jí)餐館,他的笨手笨腳引發(fā)的一系列意外給餐館造成了混亂。影片中探訪(fǎng)的原因不明,也沒(méi)有進(jìn)一步的戲劇發(fā)展,甚至是有始無(wú)終的,所以更接近于某種散漫無(wú)目的的游蕩。
于洛只是影片的一個(gè)元素,跟隨他的漫游,零散時(shí)刻被組合起來(lái),斷裂的空間在他的腳下被漫不經(jīng)心地串起來(lái)。有時(shí)攝影機(jī)甚至故意丟失了于洛,只是跟著人群一起探險(xiǎn)。
在漫游的過(guò)程中,于洛徒勞的走動(dòng)、奔跑、行動(dòng),卻不是為一個(gè)戲劇性的事件服務(wù)的,只是如游戲一般單純的游蕩。通過(guò)攝影機(jī)游蕩中的記錄,許許多多迷人的瞬間,從生活流中突現(xiàn)出來(lái),繼而又消失在生活流中。

《玩樂(lè)時(shí)間》
漫游者好奇地捕捉現(xiàn)代生活中短暫易逝的美,在這種敏銳的觀察中,包含的態(tài)度是對(duì)現(xiàn)代生活的迷戀。波德萊爾說(shuō),當(dāng)一個(gè)人知道如何閑逛,如何觀察時(shí),在一個(gè)大城市中有什么樣的怪事他不會(huì)發(fā)現(xiàn)?
生活的多樣性和一切生活成分忽隱忽現(xiàn)的魅力,在于洛的一次次漫游中,被清晰地呈現(xiàn)出來(lái),也包括那些塔蒂所批判的對(duì)象,消費(fèi)社會(huì)中那些無(wú)休止的玩意的發(fā)明、運(yùn)動(dòng)、媒體文化以及城市和郊外的設(shè)計(jì)。
導(dǎo)演塔蒂作為一位漫游者與熱情的觀察者,尋找并記錄現(xiàn)代生活短暫的、偶然的、過(guò)渡的美好瞬間,引導(dǎo)觀眾將平凡的日常生活看成一出永無(wú)止境的喜劇。
漫游者們不是希臘神話(huà)中冒險(xiǎn)犯難去尋找金羊毛的伊阿宋,也不是塞萬(wàn)提斯筆下對(duì)著風(fēng)車(chē)揮舞長(zhǎng)矛的堂吉訶德,他們穿街入巷,行行復(fù)行行,在平淡的世界中尋找詩(shī)意,他們是現(xiàn)代生活的英雄。